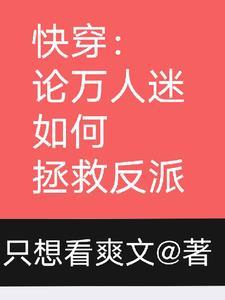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小丫鬟大少爷 > 第28章 腊月修渠(第1页)
第28章 腊月修渠(第1页)
北疆的冬夜,风如剔骨刀。
沈挽恙蜷在军营文书房的矮榻上,喉间腥甜翻涌。
他攥着胸前衣襟,指节泛白,咳得整个人都在颤抖。
案头油灯被灌进来的风吹得明明灭灭,映得他的面容更加苍白。
“咳咳……咳——”
一口鲜血溅在誊写到一半的屯田册上。
他盯着那血迹,忽然想起许怀夕昨日为他包扎冻伤时说的话。
“沈挽恙,你的手再这样冻下去,怕是连笔都握不住了。”
门帘突然被掀开,裹着风雪闯进来的许怀夕差点被血腥味呛个跟头。
她连斗篷都来不及解,直接扑到榻前,冰凉的手指掐上他腕间脉门。
“你又熬夜看图纸了是不是?”
她声音发颤,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三颗沙枣,“先把药喝了,沙枣去苦味。”
沈挽恙望着她冻裂的指尖,忽然伸手拂去她睫毛上的雪渣:“明日不必来送饭了。”
许怀夕动作一顿。
“天太冷。”他别过脸又咳了两声,“我让李校尉派人去取。”
五更鼓响时,沈挽恙已经披衣坐在案前。
许怀夕端着药碗站在门口,看他用朱砂在舆图上勾画,笔锋凌厉如剑。
“今年雪少,开春必旱。”
他头也不抬,“现在不重修这条废渠,明年饿死的就不止三五户。”
许怀夕凑近看那图纸,突然发现他标注的渠线恰好绕过她常去采药的那片荒滩。
这人竟连她走哪条路都算进去了。
“挽恙”,她轻声问,“你做这些只是为了屯田营的百姓吗?”
笔尖微微一顿,朱砂在纸上晕开一点。
“还为了某个总往狼群出没处跑的傻丫头。”
他声音很淡,“若闹饥荒,她怕是要第一个饿死。”
灶上的药罐咕嘟作响,许怀夕低头搅动汤药,藏住嘴角的笑意。
午时,许怀夕端来新琢磨的吃食。
胡麻混着荞麦面烤的薄饼,夹了腌沙葱和炙羊肉。
“你尝尝。”
她眼睛亮晶晶的,“我按您提过的长安胡饼方子改的。”
沈挽恙咬了一口,突然僵住。
这味道……竟与记忆中母亲做的胡饼有七分相似。
他从未告诉过她母亲的事,这丫头是从哪里得知的?
“好吃吗?了”许怀夕紧张地盯着他,“我试了七八次才”
她也是平时和沈老爷聊天记下来的。
只是沈老爷谈到云娘就止住了话头。
“尚可。”
他打断她,却将整张饼吃得干干净净,“明日多带一份。”
许怀夕眨眨眼:“给李校尉?”
“给你。”他取出帕子擦手,“瘦得跟柴似的,怎么扛药筐?”
帐外突然传来喧哗,有小兵满脸是血冲进来:“沈先生!守备军把咱们挖渠的人打了!”
沈挽恙起身时晃了一下,许怀夕慌忙去扶,却被他轻轻推开:“待在帐里,我让人送你回去”。
她望着他单薄的背影没入风雪,突然发现案头多了张字条
——“沙参在东南坡,别去西边狼窝”。
许怀夕在东南坡挖到一株老沙参时,月已中天。
她哼着小曲往回走,突然撞上个清瘦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