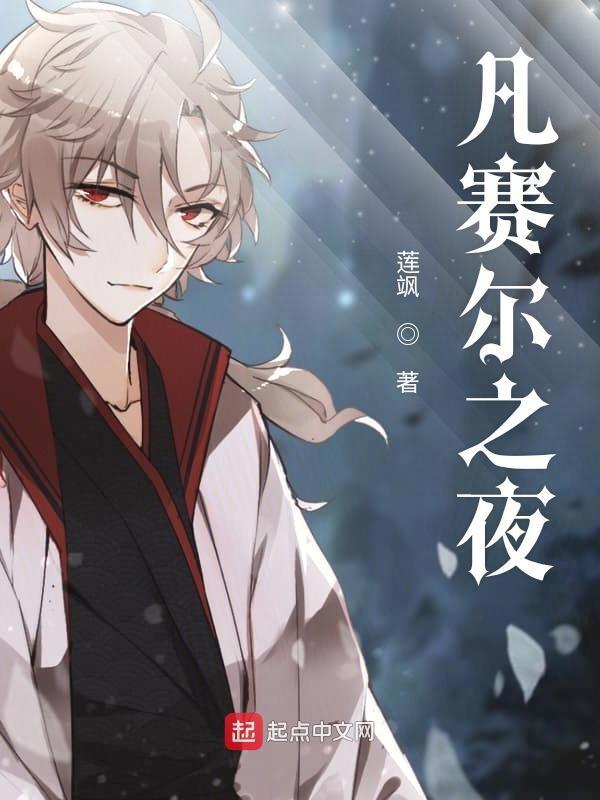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沾洲叹by诗无茶剧透 > 第105章 番外四(第1页)
第105章 番外四(第1页)
琉璃灯的灯芯从这年四月起,燃烧了二十月有余,贺兰破率领的大军直到次年年底才传出归来的消息。
祝神接过容珲从探子那儿拿到的信笺,贺兰军在北方境内最后一处战场离十六声河八百五十里,整军出发,大概元宵前后抵达。
正月十二,祝神收到贺兰破的快报,说自己三日之内到家。
贺兰破赶到十六声河那天已近傍晚,容珲早早迎在巷子口,替贺兰破牵过马后方道:“小公子先回去沐浴更衣,好好休息,吃毕了饭,二爷在长门巷信子楼等您。”
贺兰破没有第一眼看到祝神,自然是没有心思吃饭,但知自己一身尘土,还是先去房中特意洗完澡熏了香再出门。
进房时贺兰破瞧见桌台上摆着一盏青灯,大白天也点着没熄,正待问怎么回事,容珲就把事情原原本本、一字不差地告诉了他。
今儿长门巷有个大商的女儿抛绣球招亲,贺兰破到信子楼时,恰巧碰到楼下适龄男子乌乌泱泱聚成一堆,把大门整条街都堵得水泄不通。招亲是大喜的事,贸然打断也不好,贺兰破静静站在人群外,只打算等人散了再寻机进去。
不多时,二层望台上姑娘落落大方地出来,抛了绣球,接住的被迎进楼,没接住的人群一哄而散。
贺兰破还站在原来的位置,目光扫过渐渐走散的人流,挨个确定里面没有祝神。
正看着,一个掌心大的小玩意儿从天而降。
贺兰破下意识接住,摊开掌心一看,是前年他闲着没事拿兰草给祝神编的小绣球,如今已发黄了。
他抬起头,见二楼不知何时多出一个身影,正倾身倚靠在栏杆处,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祝神一身翠色衣衫,肩头披着雪白的鹤氅,也没有束发,只用一条发带在脑后随便把头发系了一下。
他一手撑着下巴,一手伸出栏杆,指尖挂着一个小小的酒瓶,对着贺兰破偏头调笑:“哪家的小公子,出来招摇,好生俊俏。”
贺兰破仰头同他对视半晌,嘴角微微一扬,伸出双臂。
祝神弯了弯眼,下一瞬,只听袖袍翻飞,人便已稳稳落入贺兰破怀中。
瓶中无酒,祝神也没去搂贺兰破的脖子,只把双手交叠着搭在自己身上,手中握着酒瓶,乜斜着贺兰破问道:“在这儿站了许久,是找不到路了?”
贺兰破不言,转身抱着他往回家的方向走去,边走边道:“听容珲说,你特意为我去求了观音的琉璃火?”
祝神收了笑:“容珲多嘴。”
贺兰破又问:“无界处来的神使,喜欢那枚玉佩,你不肯给?”
祝神道:“神使贪心。”
“你因为想我,还病了一场?”
“我身体差。”
贺兰破沉默一瞬,看向怀中,淡淡吐出两个字:“……家夫?”
祝神身体一僵。
那日扶灯一时好奇偷了他的金镶玉,他厚着脸皮要回来,一时心急,只想把情况说得严重些,便同对方说这东西是家夫之物,不料后方的容珲把这话也听了去,竟还原封不动地状告给了贺兰破。
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没点规矩了。
上方传来贺兰破的声音:“说谁?”
祝神骤然回神,惊觉自己竟把心中所想给说了出来。
他睨着贺兰破冷冷一笑:“谁要上房揭瓦就说谁。”
贺兰破忽然将他往怀中一带,一股幽幽的山空香气沁入鼻端。
祝神埋脸在他衣领前,正当问他是几时叫人从贺兰府送来的熏香,就见贺兰破脚下步子一转,往背离喜荣华的另一个方向去了。
不多时,祝神便反应过来,这正是去往喜荣华后方那间小木屋的路。
那屋子正干净着——祝神前两日不知怎么想的,许是心灵福至,派人把那里里里外外打扫收拾了一番,所有用具一概换了新,连被褥的料子和花样他都亲自选好让新做了一份。
哪晓得贺兰破进了院子,抬脚把栅栏的门踢上,并未去到房中,而是抱着祝神径直往院中那方小石桌子去。
祝神心道不妙,抓住贺兰破的肩,佯装镇定道:“做什么?”
贺兰破把人放在桌上,并未去解祝神的披风,而是一把攥住祝神的腰带,就这么扯开:“揭瓦。”
祝神推开贺兰破作势要逃:“那也得到房里去。”
又被贺兰破一掌按在身下:“就在这里。”
祝神无奈:“小鱼……”
腿却是已被分开了。
今日天气回了暖,夜间寒风却吹得紧,祝神身后披着鹤氅,氅下衣物却被尽数剥落,唯一能依附的火热只有贺兰破的身体。
起先他还想躲,衣服真落尽了,也只能往贺兰破怀里躲,如此倒有些迎合的意思。
贺兰破正是拿捏了这点,一夜到凌晨酣畅淋做了个爽,只在院中做了一次后怕祝神受不住冻,把人抱进房中,除去那件下半部分被打湿的大氅再接着办。
祝神次日下午醒来,勉强撑着床褥坐起身,看着身板挺拔站在床边系袖扣的贺兰破,暗暗决定明天就把喜荣华的瓦全换成木头,看贺兰破以后上哪揭去。
对方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只微微侧过头,窗外丝丝缕缕的光线给贺兰破衬出一张线条冷硬的侧脸:“瓦揭完了,今夜上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