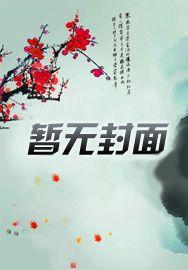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佛学研究十八篇百度 > 那先比丘经书(第1页)
那先比丘经书(第1页)
=《那先比丘经》二卷,失译人名,附东晋录。此经今巴利文有之,名曰《弥兰问经》,盖全经皆记弥兰王与那先问答语。巴利本从问者得名,汉译本从答者得名也。弥兰王亦译毕邻陀王(真谛译《俱舍论》)、曼邻陀王(玄奘译《俱舍论》)、难陀王(《杂宝藏经》)。其时代盖介于阿育与迦腻色迦两王之间,为佛法有力之外护。然彼王乃希腊人,非印度人也,经首叙弥兰受生因缘,云:“生于海边,为国王太子。”又篇中问答有云:
那先问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万里。”
阿荔散即阿历山大之对音,然则弥兰王生地,或即今之阿历山大利亚耶?时其地已役属罗马,故又云大秦国也。经又言弥兰为天竺舍竭国王,舍竭即《大唐西域记》之奢羯罗,即磔迦国故城,东据毗播奢河,西临信度河,盖迦湿弥罗(罽宾)东南境之一大国也。近欧人因研究印度古钱币,发现此王遗币二千余枚,证其确为希腊人而来自中亚细亚者。盖其币用波斯之标准重量,阳面刻希腊文,阴面刻印度文,币文中此王名弥难陀,故《杂宝藏经》亦称为难陀王也。其时代则在迦腻色迦以前,约当西历纪元前一世纪半。《后汉书·西域传》称西汉时,“月氏北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即希腊种,然则弥兰之祖父(经称弥兰为合竭太子,故知其席先业也),或即被迫于月氏,而由巴忒利亚(大夏)君迦湿弥罗(罽宾)者耶?《西域记》又言:“此国有王号摩醯逻矩罗,唐言大族,矫杀迦湿弥罗王而自立。”大族王与弥兰血统关系如何,今不可考。但大族王仇教特甚,《西域记》称其“宣令五印度,佛法并皆毁灭”。彼能宣令五印,则五印半役属于彼可知,想佛法受轹深矣。而弥兰遗币,皆刻“弘法大王弥兰”等语,殆受那先诱道后,发心皈依耶?
那先为那伽犀那之省译,此名龙军,为十六大罗汉之一,见《梵网经述记》。本经首叙其受生因缘云:“生于天竺罽宾县。”然则彼盖迦湿弥罗人矣。那先(龙军)所著有《三身论》,曾有译本,今佚。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一)云:
那伽犀那,此云龙军,即是旧翻《三身论》主。彼说佛果唯有真如及真如智、无色声等粗相功德。坚慧论师及金刚军,皆同此说。(慈恩《对法论疏》略同)
又慈恩《唯识述记》(卷一)云:
龙军论师无性等云,谓佛意慈悲本愿缘力,其可闻者,自意识上。文义相生,似如来说。
圆测、慈恩为奘公门下二杰,据此知当时《三身论》尚存也。彼论今虽佚,然观其以“三身”为名,自当是诠法身、报身、化身之义,其所主张“佛果唯有真如”云云,即后此《起信论》“真如缘起说”之所自出。龙军与弥兰同时,盖马鸣前百余年,即此可证大乘弘自马鸣之说,非确论矣。本经所记问答语,大抵皆小乘理解,盖开导未解佛理之弥兰,不得不如是耳。
此经之流传,(一)可以知希腊人与佛教之关系,(二)可以知北方佛教亦应受希腊文化之影响,(三)可以知大乘学派发生甚早,且其渊源实在北方,诚佛教史上一宝典也。英译本未见,据日本学者所引,似较此本为详。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图书馆学季刊》经始,同人责启超属文。启超于近代图书馆学既无所知,于中国旧目录学所涉亦至浅,不敢轻易有言也。顾夙好治佛学史,辄取材于诸家经录,屡事翻检,觉其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祐、法经、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素朴,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挥必更有进,可断言也。启超虽颇好读佛家掌故之书,然未有一焉能为深密之研究者,加以校课煎迫,勉分余晷以草斯篇,疏略舛谬之处,定不知凡几,冀借此以引起国内治目录学及图书馆学者对于此部分资料之注意,或亦不无小补也。
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属稿,十四日成。启超,清华
欲草斯论,宜先知经录之家数,及其年代存佚等。今制一表,以作基础。
元前经录一览表
明清两代,虽皆有大藏目录,然大率踵元之旧,加增入藏新书,故皆从略。尚有明僧智旭《阅藏知津》一书,半笔记体,亦不录。
表注:
[1]校者注:此书通行本名《出三藏记集》,此是别称。
[2]校者注:通行本名《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
[3]校者注:此书通行本名《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4]校者注:此书通行本名《续古今译经图记》。又原本“译”误作“释”。
[5]校者注:通行本名《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
[6]校者注:通行本名《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7]校者注:通行本名《大唐保大乙巳岁续贞元释教录》。
[8]校者注:通行本名《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北宋赵安仁等编。
[9]校者注:通行本名《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北宋吕夷简等编。在《大中祥符法宝录》和《景祐新修法宝录》之间,还有北宋唯净等编的《天圣释教总录》三卷,梁氏阙载。
[10]校者注:通行本名《大藏圣教法宝标目》。
[11]校者注:通行本名《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经录盖起于道安,慧皎《高僧传》(卷五本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祐录》亦云(卷二):“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又云(卷四):“大法远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皎、祐两书,在佛家史传中为最古,其言如此,则安公之作前无所承可知。
《祐录》中屡引《旧录》,费长房指为《安录》以前之书,后人皆沿其说。但录之出于祐公以前者皆可称旧,不必其旧于《安录》也。谓《古录》出秦时释利防,谓《旧录》为刘向所见,谓朱士行曾作《汉录》,此皆费长房臆断之说。(一)秦时有室利防赍佛经来华,说见王子年《拾遗记》,后人附会,谓“室”音同“释”,殊不知僧徒以释为姓,始于道安,秦时安得有此?况《拾遗记》本说部,非信史,又况《记》中亦并未言有目录耶。(二)东汉始有佛典,谓刘向曾为作录,太可笑。(三)朱士行三国时人,《高僧传》有传,并未言其作经录,所谓《汉录》者,殆后人依托耳。
汉时佛经目录,《长房录》不载,始见于《内典录》耳。原注云:“似是迦叶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等。”《四十二章经》已是伪书,则此录之伪更不待辨。
《安录》今虽已亡,然其全部似已为《祐录》采入,读《祐录》可以想见《安录》,犹之读班《志》可以想见刘《略》也。今略为爬罗,则《安录》之组织及内容考见者如下:
本录第一——以译人年代为次,自汉安世高迄西晋末法立,凡著录十七家二百四十七部四百八十七卷。
《祐录·新集经论录第一》之前半,皆用《安录》原文,略有增补。祐自云:“总前出经,自安世高以下至法立以上,凡十七家,并《安公录》所载,其张骞、秦景、竺佛朔、维祇难、竺律炎[1]
1、白延、帛法祖七人,是祐校众录,新获所附。”又于法护条下云:“祐捃摭群录,遇护公所出,更得四部,《安录》先阙。”今将《祐录》中除出张骞以下七人所译(此七家殆皆伪书),又除出护译之四种八卷(原注“安录阙”者),所得部数卷数如右,殆即《安录》之旧。
失译录第二——不知译人姓名者,凡百三十四种。
凉土经录第三、关中异经录第四——亦无译人姓名,但能知其译地,凉土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关中二十四部二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