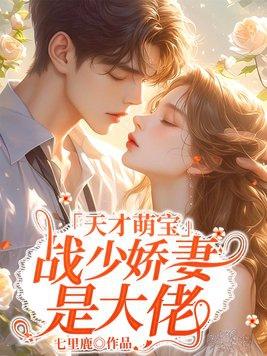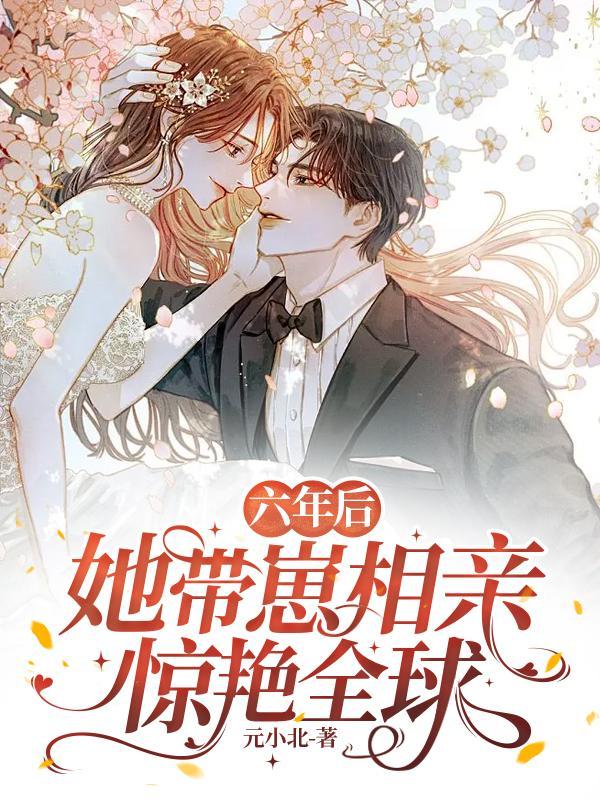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佛学研究十八篇评价 >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原题印度之佛教(第2页)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原题印度之佛教(第2页)
轮回,梵文Samsara,直译之则流转之义。佛所说轮回,并非如现在和尚们或妇人女子们所揣想,各人有一个灵魂,死后“灵魂出壳”跑到别个地方去变人变猪变狗,像炮弹子从炮膛打出去打到别处。这种话是外道的“神我说”,与佛说最不能相容。关于这一点,在下文讲“无常无我”那一节再详说。现在先说佛的轮回说之大概。
依佛的意思,人生时时刻刻都在轮回中。不过有急性,有慢性。慢性的叫做“生灭”或叫做“变异”,急性的叫做“轮回”(轮回不过各种变异形式中之一种)。你看,我们肉体,天天变化,我身上的骨肉血,不到一个礼拜已经变成了街上的粪泥尘。何止生理上如此,心理上的活动,还不是时时刻刻变迁。现在站在讲堂上的梁启超和五十年前抱在他母亲怀里的梁启超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也很可以发生疑问。这种循环生灭之相,我们便叫他做轮回也可以。不过变异得甚微而且甚慢,我们不觉得、不惊异。这种循环生灭,常人以为到死时便全部停息,依佛的观察则不然。只要业力存在,生灭依然相续。不过经一个时期,画一个段落,到那时忽然现一种突变的状态。这种突变状态,给他一个特别名词叫做轮回。有位黎士德威夫人Mrs。RhysDavids做一个图形容得甚好:
譬如A是假定的一个人本来的性格,他时时刻刻活动不休,活动的反应(即业)渐渐添上别的新成分,变为A',次第往前活动去。从前的业依然保留,随时又添上新的变为A'’、A'’’,到最后把这一个时期的经验都积集起来变为An,便是这一期生命所造业的总和。这个人的肉身,受物理原则的支配,到某时期当然会死去,但An的业依然不灭。得个机会,他便变而为Bc。其实B是An突变而成。表示他突变的关系,可以写为“anB”。以后“bnC""cnD""dnE”递续嬗变下去,都是如此。从表面看,ABCD截然不同形,实则B的原动力由A来,A'A'A''’’的种种业,都包含在B之中。A为B因,B为A果。所谓三世两重之因果便是如此。这样看来,轮回恰像蚕变蛹,蛹变蛾。表面上分明三件东西,骨子里原是一虫所变。说蚕即蛾也不对,说蚕非蛾也不对;说蛾即蚕也可以,说蛾非蚕也可以。
还有一个譬喻。一棵树经一期的活动,发芽、长叶、开花、结子,子中所藏的核,便将这树所有特性全部收集在里头。表面上看,核里一无所有,叶也没有,花也没有,但他蕴藏着那能引起开花发叶的“业力”,所以碰着机缘(例如种植)便会创造出一棵新树。新树与旧树,也类似一种轮回了。假定这核系桃核,栽出来的新树当然也是桃,不会变做李。但是,倘使换一块地土去栽,另用一种新肥料培养他,将来所结桃果,便会别是个味儿。假使把苹果树给他接上,那桃又必带有苹果味。将来把这个新核再栽出新树,又必结出带苹果味的桃子。这个譬喻,可以说明佛家所谓“种子现行相熏相引相生”的道理。桃核即“种子”,即十二因缘第一支之“无明”。核是前身桃树的结晶,把旧桃的特性(即业)全部收集在里头,故亦称业种。无核则新桃不会发生,所以说“一切众生皆由业转”。核的本身蕴藏有开枝发叶的原动力,便是第二支的“行”。假使那核煮过或泡过,种子焦了烂了,失却原动力,便不会生长。原动力是种子能发生的条件,所以说“无明缘行”。无明是种子,行是种子固有之属性,所以两项可以统名为种子。这两项都是从过去世遗传下来,新桃树未出现以前,核的本身自有这种作用,这便是能生的因。那核栽在地下,本身的原动力将他所含特性发动起来和外界环境相感应,于是发芽长叶开花结子乃至叶落根枯到这树的一期生活修了,都谓之“现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都是现行的变化。种子靠现行的熏习力才能逐渐开发,否则核只是核,不会发芽,芽只是芽,不会长叶、开花等等。现行也靠种子的熏习力才会跟着自己特性那条线上开发上去。桃核开发出的是桃不是杏,杏核开发出的是杏不是梨。这便是种子现行相熏相引。一期生活的现行中,内力受外界刺激起种种反应,原种子也跟着变化。渐渐形成这一期的新特性。例如桃树接上苹果,便成了含有苹果成分的特种桃。此外因气候、土质、肥料、人工等等之特殊,所资以形成其特性者不知凡几。这种特性总合起来——即“业”之总和,全部分又蕴藏在新结的核里头,为下一次别棵桃树的新种子。十二支的最末两支——“生”、“老死”,即他所生的未来之果。这便是前节说的“三世两重因果法则”。拿现在的话讲,种子可以勉强说是遗传,现行可以勉强说是环境(但佛家所谓种子现行比生物学家所谓遗传环境涵义更广)。禀受过去的遗传,适应于现在环境为不断的活动。活动的反应,形成新个性,又遗传下去。业与轮回的根本理法大概如此(注意,拿树来比人,总是不对,因为树是没有意识的。所以“识缘名色,名色缘识”的道理,拿树譬喻不出来。人类活动以“识”为中枢。识之活动范围极广大,事项极复杂。种子受熏习而起的变化,亦与之相应。当然不是一棵树一期生活之变迁所能比了)。
我们若相信佛说,那么,我们的生命,全由自己过去的业力创造出来,也不是无因而生,也不是由天所命。在这生命存在的几十年间,又不歇地被这业力所引,顺应着环境,去增长旧业,加添新业。一切业都能支配未来的生命。近之则一秒一分钟后一日后一年后几十年后的未来,远之则他生永劫的未来,循自业自得的公例,丝毫不能假借。尤有当注意者两点。(一)佛说的业果报应是不准抵消的,并非如袁了凡功过格所说做了一百件过再做一百件功便可以冲抵。例如今日做过一件杀人的恶业,将来一定受偿命的恶报,没有法子能躲免。明天重新做一件救人的善业,等前头的恶报受完了,善报自然会轮到头。譬如打电报,北京局里打出一个a字,上海局里立刻现出一个a字,再打b字,那边自然又现出b字,却不能说后来有个b便把从前的a取消。又如电影片,照过一个丑女,到映演时丑女定要现出来,并不因为后来再照一个美人,便能把丑形盖过。(二)佛说的业果报应不是算总账的,并非如基督教所说到世界末日耶稣复生时,所有死去的人都从坟墓里爬出来受审判,或登天堂或下地狱。因为佛的生命观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所以除却把账簿一笔勾销时,时时刻刻都是结的流水账。因能生果,果复生因。横看则因果重重,竖看则因果相续。绝不会有停顿着等结总账的时候。关于这一点,在下文“无常无我”那一节再予说明。
以上所说,业与轮回之意义大概可以明白了。依我所见,从哲学方面看,此说最为近于科学,最为合理。因为我们可以借许多生物学上、心理学上的法则来烘托证明。从宗教或教育方面看,此说对于行为责任扣得最紧而鼓舞人向上心又最有力,不能不说是最上法门。
无常与无我 佛教三法印:“(一)诸行无常,(二)诸法无我,(三)涅槃寂静。”什么是无常?佛说:“凡世间一切变异法、破坏法皆无常。”世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变异的破坏的,显而易见,地球乃至恒星系,天天在流转变迁中,再经若干千万年终须有一天毁灭。人生更不消说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何止生理上如此,从心理上看,后念甫生,前念已灭,所谓“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所以后来唯识家下一个妙喻说:“恒转如瀑流。”拿现在事物作譬,最确切的莫如电影。人之一生,只是活动和活动的关系衔接而成。活动是没有前后绝对同样的,也没有一刻休息,也没有一件停留。甲活动立刻引起乙活动,乙活动正现时,甲活动已跑得无影无踪了。白布上活动一旦停息,这一幕电影便算完。生理心理上活动一旦停息,这一期生命便算结束。活动即生命,除却活动别无生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的“如实相”,确是如此。
与无常论连带而起的便是无我论。寻常人认七尺之躯为我,印度诸外道多说有“神我”。佛则以为一切有情之生命皆由五蕴合成。五蕴复分为二:一、物质方面:即色蕴,亦名为“色”;二、精神方面,即受、想、行、识四蕴,统名为“名”。生命不过物质、精神两要素在一期间内因缘和合,俗人因唤之为“我”。今试问我在哪里?若从物质要素中求我,到底眼是我呀,还是耳是我、鼻是我、舌是我、身是我?若说都是我,岂不成了无数的我?若说分开不是我,合起来才成个我,既已不是我,合起来怎么合成个我?况且构成眼、耳、鼻、舌、身的物质排泄变迁,刻刻不同,若说这些是我,则今日之我还是昨日之我吗?若从精神要素中求我,到底受是我呀,还是想是我、行是我、识是我?抑或合起来才成我,答案之不可通,正与前同。况且心理活动刻刻变迁,也和物质一样。此类之说,所谓“即蕴我”说(求我于五蕴中),其幼稚不合理,无待多驳。还有“离蕴我”说(求我于五蕴外)。例如道教所说有个元神可以从口里或额门里跑出跑进,又或尸解后成了神仙来往洞天福地,又如基督教说的灵魂永生,当时印度外道所谓神我,亦即属此类。此类神我论,在事实上既绝对没有见证,用科学方法去认识推论又绝对不可能。佛认为是自欺欺人之谈,不得不严行驳斥(欲知佛家对于有我论之详细辩驳,可读《成唯识论述记》卷一、卷二)。想明白佛教无我论的真谛,最好还是拿电影作譬。电影里一个人的动作,用无数照片凑成,拆开一张一张的片,只有极微的差异,完全是呆板一块纸;因为电力转得快,前片后片衔接不停的动,那动相映到看客的眼帘,便俨然成了整个人整匹马的动作。“恒转如瀑流”的人生活动,背后俨然像有个人格存在,就是这种道理。换句话说,一般人所指为人格、为自我者,不过我们错觉所构成,并没有本体。佛家名之为补特伽罗Pudgala译言“假我”,不是真我。要而言之,佛以为在这种变坏无常的世间法中,绝对不能发见出有真我。既已无我,当然更没有我的所有物。所以佛教极重要一句格言曰:“无我无所。”
无常、无我,佛用他的如实知见观察人生实相,灼然见为如此。然则这样的人生,他的价值怎么样呢?佛毅然下一个断语说是“一切苦”。在无常的人生底下,一切都不得安定。男女两性打得滚热,忽然给你一个死别生离;功名富贵震耀一时,转眼变成一堆黄土。好像小孩子吹胰子泡,吹得大大的五色透明可爱,结果总是一个破灭完事。你说苦恼不苦恼?在无我的人生底下,一切自己作不得主,全随着业力驱引。虽说是用自己意志开拓自己命运,然自己意志,先已自为过去业力所支配,业业相引。现前的行动又替将来作茧自缚,尘尘劫劫,在磨盘里旋转不能自拔。你说苦恼不苦恼?所以佛对于人生事实的判断,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对于人生价值的判断说“一切苦”。
解脱与涅槃 这样说来,佛教岂不是纯粹的厌世主义吗?不!不!不!佛若厌世,何必创这个教?且天下也从没有以厌世为教而可以成一个教团,得大多数人之信仰且努力传播者。佛教当然不是消极的诅咒人生,他是对于一般人的生活不满足,自己别有一个最高理想的生活,积极的闯上前去。最高理想生活是什么?曰涅槃。怎么才能得到涅槃?曰解脱。
解脱,梵名木叉Moksa,译言离缚得自在。用现在话解释,则解放而得自由。详细点说,即脱离囚奴束缚的生活,恢复自由自主的地位。再详细点说,这些束缚,并非别人加之于我,原来都是自己找来的,解脱不外自己解放自己。因为束缚非自外来,故解脱有可能性。亦正唯因束缚是自己找的,故解脱大不易,非十分努力从事修养不可。
佛教修养方法,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随缘对治。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如三学——戒、定、慧;四圣谛——苦、集、灭、道;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等,今不必具述。要其指归,不外求得两种解脱。一曰慧解脱,即从智识方面得解放;二曰心解脱,即从情意方面得解放。我们为讲解便利起见,可以分智、情、意三项为简单的说明。
(一)智慧的修养。佛教是理智的宗教,在科学上有他的立场。但却不能认他是主知主义派哲学。他并非如希腊哲学家因对于宇宙之惊奇而鼓动起研究热心。“为思辩而思辩”的议论,佛所常呵斥也。佛所谓智慧者,谓对于一切“世相”能为正当之价值判断,根据这种判断更进求向上的理想。《心经)说:“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乃至……无挂碍……无有恐怖。”【《心经》此段的原文为:“……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般若译言智慧。一面观察世相,深通因缘和合、无常无我之理,不受世俗杂念之所缠绕;一面确认理想界有高纯妙乐之一境,向上寻求。佛家所用各种“观”全是从这方面着力。
(二)意志的修养。意志修养有消极、积极两方面。消极方面,主要在破除我执,制御意志,换句话说,要立下决心,自己不肯做自己奴隶。佛以为众生无明业种,皆由对于我的执著而生,因为误认五蕴和合之幻体为我。既认有我,便有“我所”,事事以这个假我为本位。一切活动,都成了假我的奴隶。下等的替肉体假我当奴隶,例如为奉养舌头而刻意求美食,为奉养眼珠而刻意求美色之类。高等的替精神假我当奴隶,例如受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或见解所束缚而不能自拔之类。佛以为此等皆是由我执发生的顽迷意志,我们向来一切活动,都为他所左右。我们至少要自己当得起自己的家,如何能令这种盲目意志专横?非以全力克服他不可。后来禅家最爱说“大死一番”这句话,就是要把假我观念完全征伏,绝其根株的意思。
但佛家所谓制御意志者,并非制止身心活动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之谓。孟子说:“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一方面为意志之裁抑,他方面正所以求意志之昂进。阿难说:“以欲制欲。”(《杂阿含》三十五)佛常说“法欲”,又说“欲三昧”。凡夫被目前小欲束缚住,失却自由。佛则有一绝对无限的大欲在前,悬以为目标,教人努力往前蓦进。所以“勇猛”、“精进”、“不退转”一类话,佛常不离口。可见佛对于意志,不仅消极的制御而已,其所注重者,实在积极的磨炼激励之一途。
(三)感情的修养。感情方面,佛专教人以同情心之扩大,所谓“万法以慈悲为本”。慈谓与人同喜,悲谓与人同忧。佛以破除假我故,实现物我同体的境界。对于一切众生,恰如慈母对于爱子,热恋者对于其恋人,所有苦乐,悉同身受。佛以为这种纯洁的爱他心必须尽量发挥,才算得佛的真信徒。以上所说,算是佛教修养的大纲领。因讲演时间太短,只能极简略的说说罢了。为什么要修养呢?为想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境界。这个境界,佛家名曰涅槃。
涅槃到底是什么样境界呢?佛每说到涅槃,总说是在现法中自证自知自实现。我们既未自证自现,当然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依训诂家所解释,大概是绝对清凉无热恼,绝对安定无破坏,绝对平等无差别,绝对自由无系缚的一种境界。实相毕竟如何,我便不敢插嘴了。但我们所能知道者,安住涅槃,不必定要抛离尘俗。佛在菩提树下已经得着涅槃,然而还说四十九年的法,不厌不倦,这便是涅槃与世法不相妨的绝大凭据。
附录说无我
佛说法五十年,其法语以我国文字书写解释今存大藏中者垂八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无我”。
佛何故说无我耶?无我之义何以可尊耶?“我”之毒害,在“我爱”、“我慢”,而其所由成立则在“我见”。何谓我爱?《成唯识论》(卷四)云:“我爱者,谓我贪,于所执我,深生耽着。”我爱与兼爱不相容,对于我而有所偏爱,则必对于非我之“他”而有所不爱,如是则一切世界不成安立。我身、我妻子、我家族、我财产、我乡土、我团体、我阶级、我国家,如是种种,认为是即我或我所有,从而私之,其他身、他家族,乃至他阶级、他国家,以非我故,对之而生贪悭、嫉妒、怨毒、欺诈、贼害、斗争,以是之故,一切世界,不成安立。何谓我慢?《成唯识论》云:“我慢者,谓倔傲,恃所执我,令心高举。”万事以我为中心,以主我的精神行之,谓环乎我者皆宜受我支配,供我刍狗;其浅狭者,如个人的我慢、阶级的我慢、族姓的我慢、国家的我慢,且不必道;其尤普遍而深广者,则人类的我慢,谓我为天帝之胤,为万物之灵,天地为我而运行,日月为我而明照,含生万类为我而孳育。以五官所经验,谓足穷事物之情状;以意境所幻构,谓足明宇宙之体用,故见自封,习非成是。湮覆真理,增长迷情,我爱我慢,其毒天下如此。至其为个人苦恼之根源,更不必论矣。而其所由起,则徒以有我之见存,故谓之“我见”。不破此我见。则我爱与我慢,决末由荡涤,此佛所以以无我为教义之中坚也。
所谓“无我”者,非本有我而强指为无也。若尔者,则是为戏论,为妄语。佛所断不肯出。《大智度论》三十六云:“佛说诸法性常自空,非以‘空三昧’令法空。”佛之无我说,其所自证境界何若,非吾所敢妄谈。至其所施设以教吾人者,则实脱离纯主观的独断论,专用科学的分析法,说明“我”之绝不存在。质言之,则谓吾人所认为我者,不过心理过程上一种幻影,求其实体,了不可得。更质言之,则此“无我”之断案,实建设于极隐实、极致密的认识论之上。其义云何?即有名之“五蕴皆空说”是已。今当先释五蕴之名,次乃述其与“我见”之关系。
蕴Khandha,旧译阴,亦译聚,亦译众。《大乘广五蕴论》云:
问:蕴为何义?答:积聚是蕴义,谓世间相续,品类趣处差别色等总略摄故。如世尊说,比丘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胜若劣,若近若远,如是总摄为一“色蕴”。
(今译)问:什么叫做蕴?答:蕴是积聚的意思,将时间的相续不断之种种差别现象,分出类来,每类作为一聚,这便是蕴。例如世尊告某比丘说,所有一切物质(色),现在的、过去的、未来的,内的、外的,粗的、细的,胜的、劣的,远的、近的,总括起来,成为一个“色蕴”。
蕴训积聚,故凡有积聚义者皆得名蕴(例如篇名亦谓之蕴,《发智论》、《大毗婆沙》皆分八蕴,即八篇也。旧译取梵音名八犍度)。此所谓蕴者,专就意识活动过程上之类聚而言,凡分为五。
以上所释,尚有未明未惬之处,更分释如下:
(一)色蕴《增一阿含经》(廿八)云:“此四大身,是四大所造色,是故名为色阴。……所谓色者,寒亦是色,热亦是色,饥亦是色,渴亦是色。”《大乘广五蕴论》云:“云何色蕴?谓四大种及大种所造色——无表色等。”色蕴所摄如下图:
说明:四大种指物质,四大所造色指物质之运动,此二者不容混为一谈。最近倡相对论之哀定登A。S。Eddington已极言其分别之必要。“所造色”分三类。第一类五根,即《杂阿含》所谓四大身。第二类五境,即五根所接之对境。第三类无表色,分为极略、极迥、定所生、遍计所起等。极略、极迥,皆极微之意。“极略”谓将木石等有形之物质,分析至极微。“极迥”谓将声光等无形之物质,分析至极微,甚与现代物理学的分析相似矣。“定所生”谓用定力变成之幻境,如诸大乘经所说“华严楼阁”等。“遍计所起”谓由幻觉变现,如空华第二月等。合以上诸种,总名色蕴。
以吾人常识所计,此所谓色者,全属物理的现象(除无表色中一小部分)。何故以厕诸心理现象之五蕴耶?须知认识之成立,必由主客两观相对待,无主观则客观不能独存,外而山河大地,内而五官百骸,苟非吾人认识之,曷由知其存在?既已入吾识域而知其存在,则知其绝不能离吾识而独立,故佛家之谓此为识所变。论云:“谓识生时,内因缘力变似眼等色等相现,即以此相为所依缘。”(《成唯识论》卷一)又如经所说寒热、饥渴等,骤现似纯属生理的事实,其实对于此种外界之刺戟,心理的对应先起,而生理的冲射乃随其后,特此种极微细的心之状态,素朴思想家未察及耳,故吾总括此造种“色”,名之曰感觉的客观化。此义在《毗婆沙》、《俱舍》、《瑜伽》、《唯识》诸书,剖之极详,得近世欧美心理学者一部分的证明,更易了解。
(二)受蕴经云(《增一阿含》廿八,下同):“受者名觉。觉为何物?觉苦,觉乐,觉不苦不乐。”《广五蕴论》云:“受,谓识之领纳。”与色蕴相应之寒热、饥渴等,不过受刺激之一刹那间,为纯任自然之对应,不含有差别去取作用;再进一步,则在并时所应之无数对境中,领受其某部分,例如冬令,围炉则觉受“热色”而起乐感,冒雪则觉受“寒色”而起苦感,是之谓受,当心理学书所谓感觉。
(三)想蕴经云:“云何名想阴,所谓三世共会。……想亦是知,知青、黄、白、黑,知苦知乐。”《阿毗昙杂心论》云:“想者,谓于境界能取像貌。”(《广五蕴论》原文如下:“想者,于境界取像貌。”)此所谓想者,不应解作广义的“思想”,盖仅能摄取事物之像貌,如照相机而已。然摄取一像貌,必须其像貌能示别于他像貌,则非有联想的作用不为功。经言三世共会者,三谓过去、现在、未来,共会者,即联想之义。何以能知青、黄、白、黑?前此本有如何是青的概念,现在受某种“表色”则知其与旧所记忆之青的概念相应,而示区别于其他之黄、白、黑,此即所谓知觉。而其所得,则印象也。
(四)行蕴经云:“所谓行者,能有所成……或成恶行,或成善行。”行蕴所含最广,心理现象之大部分皆属焉。今依《大乘五蕴论》及《百法明门》,以百法中之九十四有为法,分配五蕴,列为下表,读之可以知行蕴内容之复杂焉。
说明:法字按诸今语,可译为概念。百法之名,非佛时所有。佛常言一切法,而未举其数。小乘家如《俱舍论》等,举七十五法。大乘家如《瑜伽师地论》等,举六百六十法。此所依《百法明门》,乃天亲撮瑜伽为略数。此皆将心理现象绵密分析,近世欧美斯学专家,尚不逮其精审。百法中除六种无为法超绝五蕴外,余九十四种有为法,大分为四类:一心法,二心所法,三色法,四不相应法。此中复分为二系,心法自为一系,即能认识之主体,余三类合为一系,即所认识之对象。彼三类中,色法即物理的对象。心所法者,谓“心之所有”,即心理之对象也。不相应法者,谓与色与心俱不相应,如生命、语言文字等皆属之。
此诸法中,心所法与不相应法最为复杂,共占七十五种。以配五蕴,则除此中两种分属受蕴、想蕴外,余七十三种俱属行蕴,此可见行蕴之内容矣。
观上表则知行蕴所摄,殆亘心理之现象之全部。欲概括说明,颇极不易,但其中最要者,为遍行法中之触、作意、思三种(遍行法有五:一作意,二触,三受,四想,五思。此据《百法明门》次第。受、想各分属其本蕴,余三属行蕴,如上表。)依《广五蕴论》所释“触谓眼、色、识等三和合分别”,【《广五蕴论》原文如下:“云何触?谓三和合,分别为性。三和,谓眼、色、识,如是等。此诸和合,心心法生,故名为触。”】谓眼根、色境、眼识凑会在一处,乃成为“触”也(此色字非色蕴之色,此触字非色、声、香、味、触之触,勿混)。“作意……谓令心、心所法现前警动。”即今语所谓特别注意。“思,谓令心造作意业,犹如磁石引铁令动。”是知“行蕴”者,对于想蕴所得之印象加重主观的分量,经选择注意,而心境凝集一点,完为一个性的观念也。故曰“能有所成”。
(五)识蕴识蕴,小乘谓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大乘加以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是为八识。《广五蕴论》云:“云何识蕴?谓于所缘了别为性,亦名心,亦名意,此能采集诸行种子。又此行相不可分别,前后一类相续转。”【《广五蕴论》原文如下:“云何识蕴?谓于所缘,了别为性。亦名心,能采集故;亦名意,意所摄故。若最胜心,即阿赖耶识,此能采集诸行种子故。又此行相不可分别,前后一类相续转故。”】《顺正理论》(卷三)云:“识谓了别者,是唯总取境界相义,各各总取彼彼境相,各各了别谓彼眼识,虽有色等多境现前,然唯取色,不取声等……于其自境,唯总取相。”法相宗书数百卷,不外说明一“识”字,繁征细剖,恐读者转增迷惘,且俟下文随时诠释。今但以极简单语略示其概念:识也者,能认识之自体,而对于所认识之对象,了别其总相,能整理统一个个之观念使不相挠乱,又能使个个观念继续集起不断者也。其实色、受、想、行,皆识所变现,一识蕴即足以包五蕴,所以立五名者,不过施设之以资观察之便利,谓意识活动之过程,有此五者而已(所谓七十五法、百法乃至六百六十法,皆不外一种方便的施设,但求不违真理,名数不妨异同)。试为浅譬如印刷然,色蕴为字模;受、想、行则排字之次第,经过逐段递进,识蕴则纸上之印刷成品,机器一动,全文齐现。此譬虽未悉真,亦庶近之。
佛典屡用色、名二字,色即指色蕴,名指受、想、行、识四蕴。因其为方便施设之一种名号也。此则前一蕴为一类,后四蕴为一类;若就能所区别论,则前四蕴为一类,后一蕴为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