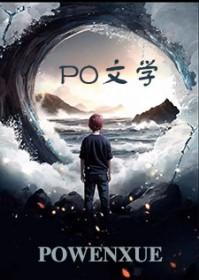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王妃主动示好 > 第83章 贪生怕死(第2页)
第83章 贪生怕死(第2页)
自打纪渊说了他身边的人能够做翻译之后,顾寒书拒绝的心就更加坚定了。
赈灾之事,山高路远,说不得已耽误了多久。
此去西南,若是百姓及时得救,甚至不能得赏,若叫黎民百姓损失惨重,便是要赔的血本无归,连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名声也要再加上草包二字!
顾寒书又怎肯拿自己的名声去冒险?
他话音一落,身后的吏部侍郎就站了出来。
他是如今只有五岁的太子的外祖父,素来清正廉明,只是性子冷硬些,便直截了当反问:“摄政王难道连这等救济天下百姓的事都不愿意去吗?”
“太。祖皇帝曾说,君王都该爱民如子,若无当初先帝开恩垂怜,留下王爷在京城辅政,只怕以王爷的本事,也早就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了!”
“那西南之地本就是王爷的封地,王爷不回去照顾自己封地内的百姓,却在京城蹉跎时光做什么?难道王爷原先所说的忧国忧民竟都是假的吗?”
“摄政王这三个字,可不是摆在明面上的空谈,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众大臣私下里可都等着看王爷的做派呢!”
这一下子,把顾寒书逼得进退两难。
他下意识把目光飘向旁边的礼部尚书身上。
礼部尚书是三皇子的外祖父,太子与三皇子之间就仅隔了一年,但三皇子母家人明显会做事圆滑点,从不肯得罪任何一个人,更是把顾寒书维护的极好。
那礼部尚书只感头痛,高举笏板,挡住了自己半张脸,不愿掺和进这场灾难中去。
这下子,太子一党的官员更是跳脚叫嚣。
“此事如何能儿戏?摄政王当初讨了个好媳妇,在姜家军的功劳保证下才坐在了摄政王的位置,您若不励精图治,难道不更叫人认为摄政王这个名字是靠讨好女人得来的吗?”
顾寒书的脸色黑成一团。
当年,他就曾遭遇过这样的闲话,没想到,如今时过境迁,这样的话,竟然又来了一遍!
站在众人眼前,顾寒书明明衣着齐整,可他却总觉得自己像是被人剥去了衣裳,赤身luo体的站在这里,享受着旁人的审判一般。
许久,他无奈叹一口气,轻声道:“本王可什么都没说。”
然而他说不说的并不打紧,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朝堂上的官员们一块吵作了一团,一半是支持顾寒书前去赈灾,另一半则是骂他德不配位,靠吃女人的功劳才坐上摄政王的位置,贪生怕死!
顾寒书迫于无奈,只得紧咬牙关,勉强应下了亲自领兵去西南赈灾的要求。
他松口的一瞬间,姜瑾和几个熟识的将领对视一眼,都是一笑。
姜瑾从一开始就是这个目的。
既然顾寒书留在京城里,就只会给人添乱,干脆就让他去西南好生赈灾。
万一此事做的不好,有纪渊的下人从旁做策应,总不会出大乱子,还可以在回朝之后赏罚分明的夺去他摄政王的位置,为朝廷解决一个心腹大患。
此乃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