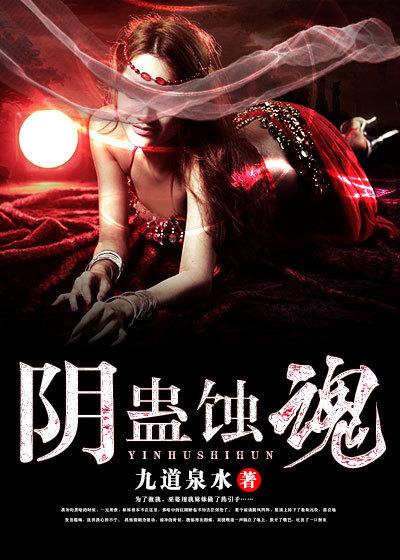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文豪193个人简历 > 第29章 口气太大(第1页)
第29章 口气太大(第1页)
《诗刊》在诗人心中的位置几乎跟《人民文艺》在文坛的地位差不多,是唯一的专业发表诗歌和诗歌评论的国家级诗歌杂志。
两者都是作协旗下的,可以说是孪生兄弟一般。两者的命运也一样,都是刚复刊不久,《诗刊》从76年复刊。
等四人棒打倒后,《诗刊》是彻底的甩开了包袱,准备大干一场。内部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只瞻前,不顾后。”
8月13日,《诗刊》的编辑正在稿子堆里面疯狂寻找稿子,一个个热的满头大汗。编辑部中间的一张空桌子上摆着一盆切好的西瓜,旁边放着吃干净的西瓜皮。
编辑部的墙上挂着编辑部的办社宗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诗歌跟小说不一样,最多也就几百字,编辑仔细地看完也就十分钟时间,基本上不会错过很好的诗歌。
当然不排除一些诗歌写的比较深奥,编辑要很费劲地才能读懂他的意思,这就比较考验编辑的诗歌分析能力了。
遇到好的诗歌,这些编辑便会旁若无人地大声地朗诵出来,让编辑部的同志一起评点一番。这要是换成了《人民文艺》的编辑,读一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就能把他们累的够呛,要是中篇,简直是要了老命了。
《诗刊》编辑邹获凡正在信件堆里面扒拉着投稿信,他不仅仅是诗人也是作家,对他来说,编辑的工作不仅不枯燥,反而让他感到很充实。
六十一岁的年纪,工作起来还是跟个年轻人一样。
他最喜欢看到的投稿信是以前诗人朋友寄过来的,可以通过诗歌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现状和目前的心理情况。
自从今年调入《诗刊》编辑部工作后,他就经常跟以前的朋友联系,得知一些人在乡下生活过得困难,也会时不时地提供帮助。
邹获凡收到投稿信会先看看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他要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朋友。
“刘一民。”邹获凡看这里刘一民的名字,轻轻地读了一下,总感觉这三个字很熟悉,但一时半会又想不起来。
于是摇了摇头不再去想,快速地打开了信封,一张小纸条率先掉落在桌面上。邹获凡好奇地打开一看,顿时乐了。
“发表请注明作者单位?汝县。。。。”邹获凡冷哼了一声,这口气未免也太大了,跟作者已经知道会必须发表一样。
“看我给不给你发表!”
邹获凡推了推老花镜,决定仔细地看一看这名作者的“大作”,看看什么样的作品能让作者的嘴跟吃了大蒜一样,口气冲天。
邹获凡甚至心里面浮现出一个恶趣味,就是不给这位作者过稿,顺便好好挑挑毛病给本人退回去。
邹获凡打开正文稿纸,戏谑地读了起来。
看到第一句,就让他有一种直冲天灵盖的震撼,捏稿纸的手不自觉地用了用力。
本来靠在椅子上看稿,随着精神的专注,不知不觉地坐直了身体。
等看到最后,猛地用手拍了一下桌子,激动地站了起来,脚踢开了身后的椅子。
这举动吓得对面的编辑一跳,大家是共用一张大桌子,他这边一拍,那边跟地震了一样,顿时一脸幽怨地看着热血沸腾的邹获凡。
只见邹获凡摆开了架势,张开臂膀,以极其夸张的肢体动作朗诵了起来: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