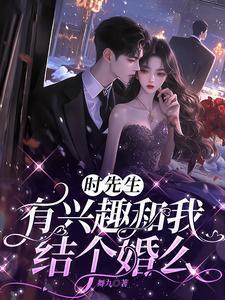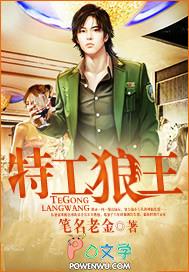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大明 逆臣列传 > 第32章 是忠是奸自有天意知晓(第2页)
第32章 是忠是奸自有天意知晓(第2页)
朱允熥略显忧虑,刑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皆被文官掌控,尽管这些官员不一定都是朱允炆的心腹,但目前看来,自己显然不受这些文官的青睐。若有机可乘,他们或许会千方百计地陷害自己。蓝玉交给他们处理,恐怕会有麻烦。
想到此处,朱允熥再次看向蓝玉与傅叶,说道:“今晚所为,是为了尽忠于皇祖父,暂且先将他们押至王府。”随后表示,次日早朝后再奏请朱元璋,再进行审问定罪。
------------
远方,方孝孺依旧关注着这里的动态。听到这段对话,他眼中顿时闪过一丝亮光,随即转身前往献王府。
夜色渐浓,原本热闹的街市很快归于平静。今日之事太过突然且意外,当朱允熥带着锦衣卫押解蓝玉和傅叶回到吴王府时,余波仍未平息。
献王府内,夜晚漆黑一片,朱允炆的书房中燃起了数十根蜡烛,照亮整个空间。方孝孺归来之际,黄子澄亦刚到达。
朱允炆急切地询问二人情况。方孝孺饮了一口茶,随后将自己在凉国公府外的经历详述一遍。最后愤慨地说:“可恶的蓝玉,我以为他一贯性格暴躁,从不容忍委屈,岂料关键时刻却胆怯懦弱,错失良机,真是可恨!”
黄子澄皱眉道:“奇怪,依我对蓝玉的认识,他绝非如此之人。”
朱允炆沉思片刻,猜测道:“难道他们事先已密谋妥当,今日之举不过是在演戏给我们看?”
方孝孺与黄子澄皆摇头否认。
方孝孺说道:“亲眼所见,今日情形危急,稍有差池,对他们而言便是无法扭转的局面。”
“若蓝玉与吴王早有预谋,演戏骗人,就不会出现王弼带领武将勋贵阻止之事。”
黄子澄点头称是:“确是如此,但此事着实古怪,蓝玉的反应超出我们意料。”
不久后,他舒展眉头笑道:“不过没关系。”
“吴王抓住蓝玉,引发如此**,差点与王弼为首的武将勋贵交恶,形成**。”
“虽然事件平息,朝廷仍需追究吴王责任。”
“我已联系御史和言官,还有几位给事中,只等明日早朝,便参他一本。”
“既参蓝玉之罪,也参吴王的胆大妄为。”
“双管齐下,定叫二人永无翻身之日。”
方孝孺抚须道:“黄兄计策极佳,蓝玉被抓只是开端,而非终结。”
“明日朝堂,全仰仗黄兄。”
“务必要一举击垮二人,扫清立献王为储君的阻碍。”
朱允炆听罢,心中兴奋不已,又问:“咱们之前的计划,是否可以一起使用?”
“莫急!”方孝孺摇头,“陛下向来偏袒至亲,即便犯下大错,也不易严惩。”
“咱们一次性使尽所有手段,陛下未必就会痛下**。”
“不如暂且留着,日复一日递上奏折,一封比一封更重,时间久了,陛下心中怒火越积越多。”
“对吴王的惩罚自然也越来越重,让他永远失去机会。”
朱允炆闻言,拜服道:“先生饱学圣贤之书,所提办法远胜他人,是我思虑不周。”
“没错,就按先生之法,必能让其自食恶果。”
朱允炆停顿片刻,又装作可怜兮兮地说:“只是这样一来,皇爷爷每日伤心难过,伤及身体,这是我不孝啊。”
方孝孺忙劝道:“献王仁孝,此时绝不能手软。”
“除掉了吴王,扫除了殿下继承皇位的阻碍,待殿下登基称帝、掌控江山、安定社稷、使万民安泰,令大明永世长存,这才是对陛下最大的忠孝。”
“若是只顾眼下不让陛下忧愁,却未能彻底清除吴王,使其有机可乘夺回江山,则是对不起陛下,对不起黎民,实为不孝。”
“若是把江山托付给他,殿下便是朱氏一族的罪人,也是天下百姓的罪人!”
朱允炆深感敬佩,说道:“先生教导甚是,学生铭记于心!”
黄子澄道:“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明日的朝会上给蓝玉和吴王定罪,这件事我们必须仔细商议。”
朱允炆点头:“正是如此,我们切不可疏忽大意。那日朝会之上,他公然要求储位,觊觎江山,却还能平安无事地离开。”
“今日之事,是他主动挑起,必定早有准备。”
“我们万不可轻视。”
方孝孺笑道:“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今晚我们立刻把蓝玉劫走,连夜审问,先给他定罪,结成铁案,顺便牵连吴王。”
“就说吴王与蓝玉****,吴王因事情败露才去捉拿蓝玉。”
“只要蓝玉承认并指证,此案就毫无争议,无人能改。”
黄子澄惊愕地说:“可是蓝玉在吴王府中,有锦衣卫守护,我们怎么抢得过来呢?”
“难道方兄能说服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吗?”
方孝孺笑着摇头:“这当然不可能。”
“不过,几年前锦衣卫的审讯和关押权就被陛下收回了,你们难道忘了?”
“现在锦衣卫的牢房早已荒废,刑具也损坏多年未曾修复。”
“吴王已经把蓝玉还有那个傅叶都关在自己的府邸里了。”
“依我看,他们今晚可能会达成协议,甚至重新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