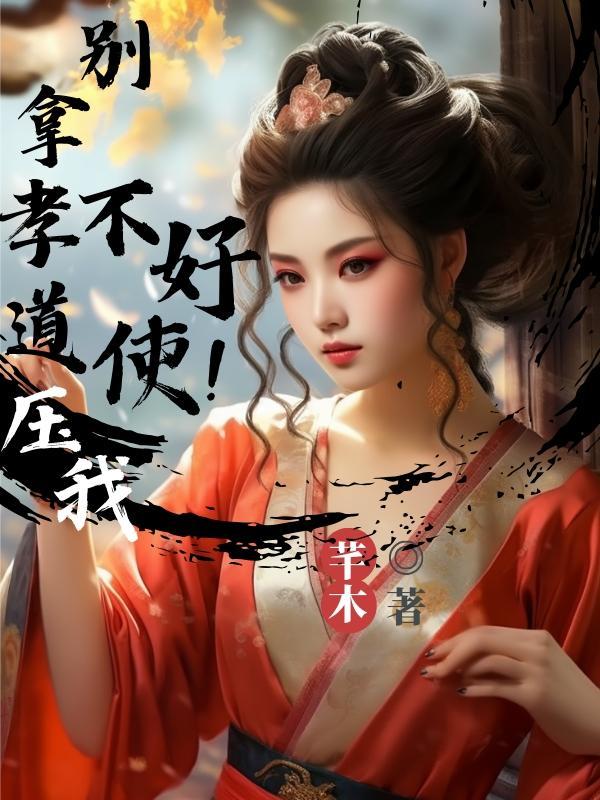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双男主非cp > 第142章 误解尽消 终迎曙光(第1页)
第142章 误解尽消 终迎曙光(第1页)
(正文)
晒谷场飘着潮湿的稻草香,郝逸辰调试投影仪时,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衬衫下的玉佩。
老式幕布被夜风吹得鼓起,映出赖诗瑶蹲在配电箱旁的身影——她正用裹着创可贴的指尖,将最后两股电线缠成麻花辫。
"当年老厨师熬糖浆烫伤的位置,和诗瑶手上金光的形状一模一样。"郝宇轩压低声音,军靴碾碎半块风干的糖霜花饼。
无人注意的幕布背面,他悄悄把军用水壶里的姜茶倒进赖诗瑶的保温杯。
第一帧画面亮起时,暴雨冲刷陶缸的闷响突然从音响里炸开。
举着蒲扇的李阿婆猛地站起来,竹椅在青石板上刮出刺耳声响。
镜头掠过祠堂飞檐下结网的燕巢,无人机俯冲拍摄的视角里,三十七个饕餮纹陶缸在晒谷场围成北斗七星阵。
"那是俺家祖传的腌菜缸!"张叔手里的瓜子撒了满地。
特写镜头正缓缓推近,陶缸内壁用朱砂描摹的星象图,与祠堂梁柱裂纹完美重叠。
画面突然插入四十年前的胶片影像——年轻的老厨师举着铜勺,月牙形烫伤在手腕泛着金光,将琥珀色糖浆浇在冬至宴最后的冰雕祭品上。
赖诗瑶把渗血的指尖藏进袖口。
当播到老厨师临终前将枣木拐杖掷入灶膛的画面时,前排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先前举着锄头闹事的赵铁柱突然冲上台,沾着泥浆的解放鞋在幕布投下巨大阴影:"俺爹当年偷藏祭器,原来是为守住祠堂地窖里的族谱"
郝逸辰刚要阻拦,却现赵铁柱颤抖着掏出个油纸包。
霉变的糖霜花饼簌簌掉落碎屑,露出夹层里半张年的《民俗保护倡议书》。
镜头适时定格在老厨师腕间伤疤的特写,那道月牙形金光与赖诗瑶正在愈合的指尖伤口,在幕布上交相辉映。
"丫头,对不住啊。"李阿婆解开蓝布包袱,取出用红绳串起的七枚古铜钱,"这是当年从你太奶奶糖勺上熔下来的"铜钱叮当落在赖诗瑶掌心时,郝宇轩口袋里的玉佩突然停止烫。
他望着人群外围悄悄离场的几个佝偻背影——那些曾在雨夜砸过摄像机的老人们,正把自家陶缸往祠堂方向搬动。
庆祝活动定在冬至正午。
郝逸辰凌晨三点就带着无人机群在晒谷场排兵布阵,螺旋桨掀起的气流惊飞了赖诗瑶晾在竹竿上的扎染围巾。
他弯腰去捡时,瞥见郝宇轩的军用吉普满载着迷彩包装箱驶入村口。
"我在苏州订的琉璃糖画灯,能投射二十四节气光影。"郝逸辰将围巾绕在赖诗瑶颈间,指尖状似无意擦过她耳垂,"某些人估计只会送军用水壶。"
赖诗瑶望着树后一闪而逝的迷彩衣角,把保温杯里的姜茶喝出了酒酿的灼烧感。
当她现郝宇轩偷偷往糯米糍粑里塞边疆特产沙枣时,郝逸辰的无人机正在她头顶拼出心形星图;等她尝出枣泥馅里藏着玫瑰糖晶,郝宇轩的退伍战友们已经用行军灶炖起了十全滋补汤。
冬至日头升到祠堂飞檐时,晒谷场变成了沸腾的民俗博物馆。
赵铁柱带着青年们舞动缀满陶铃的草龙,李阿婆们用糖霜在八仙桌上绘出星空图腾。
赖诗瑶的扎染长裙扫过青石板,裙摆掠起的气流惊动了郝逸辰悬在老槐树上的糖画灯,琉璃光影正好笼罩郝宇轩刚搭好的篝火台。
"接下来是冰雕预热环节!"村长突然敲响铜锣。
赖诗瑶感觉左右手腕同时被温热触感包裹——郝逸辰掌心的玉佩拓印着她腕动脉搏,郝宇轩指腹的枪茧正摩挲她结痂的指尖。
两人异口同声的"小心着凉"被淹没在欢呼声里,他们这才现对方给赖诗瑶披外套的动作竟如镜像般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