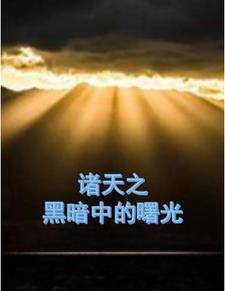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枕剑匣免费阅读 > 第67章(第1页)
第67章(第1页)
她没能?说完。
那股剧痛似乎要?将她整个人都撕裂开来,一层一层的心悸漫卷而上,让她难以呼吸,平素里还可以运三清之气?来纾解,然而此?时,她只能?任凭疼痛将自己裹挟。
那只攥住谢晏兮衣摆的手慢慢失力,软软坠地。
失去意识的前一瞬,凝辛夷的手指尖燃起了一抹灵火,那火倏而将她周身裹了起来,形成了一层极薄的守护灵阵。
谢晏兮看到了那抹灵火。
他不至于觉得凝辛夷的这一抹灵火是?她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忘要?防备他。
这更像是?她常年生活于无人可信、无人能?信的环境之中,让她即便表面看起来一切无虞,却直到山穷水尽,还要?为自己存留最后的一点自保之力。
谢晏兮收剑,再将那柄无色之剑也一并挎在?了腰间,然后才将已经失去了意识的凝辛夷扶坐在?了一块凸起的岩石上,他俯身弓腰,将她背了起来。
如若不是?此?前他借过她三清之气?,此?刻她周身的气?息都还隐约有着他的气?息,这一道看似普通的守护灵阵,他也绝不敢触碰。
谢晏兮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像是?怕惊扰背后少?女。他侧头就?能?看到她些?许颤抖的睫毛,似是?坠入了什么不安的梦境。
她的长发乖顺地垂落下来,流淌在?他的臂弯。她的体重比他想象中还要?更轻一点,但饶是?如此?,这样的角度和动作,还是?让他方才被包扎好、不再渗血的伤口裂开。
他一路走,衣袖衣摆的色彩也一路逐渐变深,但在?他终于踏出白沙堤被彭侯烙下了爪印的石门?后,所有他流落在?白沙堤的血迹,却都随着他的一回眼,燃烧了起来。
灵火如跳跃的幽蓝小鱼,没过那些?血迹,然后消失不见,不留一丝痕迹。
凝辛夷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也不知道是?不是?碰见了谢玄衣的缘故,她梦见了三清观与东序书院。
那时凝玉娆天资卓越,被辟雍书院的元君灵泉子?一眼看中,收为亲传徒弟。
她那时还年幼,又?刚刚失去了所有记忆,凝茂宏后院并不如其他世家那般多阴私,然而当家主母息夫人对她肉眼可见的不喜,她又?哪有什么好日子?能?过,素来都是?阿姐凝玉娆私下偷偷忤逆自己的母亲,对她多有照拂看顾。
长姐如母,便是?凝玉娆其实也只长她两?岁,她也自然忍不住对这偌大冷清府邸中唯一对她真心相待之人极为依赖。
因而听到凝玉娆要?离开凝府去往书院时,她顿时惴惴不安起来。
那时她尚未如后来那般,学会将真正的自己潜藏起来,于是?她也哭闹着要?去书院。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一个小小的女童。以息夫人在?后院的本?事,足以将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压下去,惹不起半点风浪。
奈何这事儿,不知被谁捅到了凝茂宏那里,凝家老爷既然亲自过问了一句,这事儿,便不能?再草草了事,糊弄揭过。
息夫人第一次将凝辛夷唤至她的暖阁,她坐在?高位,看似和颜悦色地看着跪在?下方的凝辛夷,告诉她,她是?凡体之人,即便去了书院,也只能?学经科。且不论女子?学经科有无用处,书院的书甚至还没有龙溪凝氏的藏书多,她可以请神都最好的女夫子?来为她授课。
凝辛夷去书院哪里是?想学什么,但她什么都不能?说,否则就?会暴露凝玉娆悄悄照拂她的事情。
她不依息夫人,干脆撩袍在?凝茂宏的书房门?口跪了足足三日,才终于坐上了去东序书院的马车。
她知道,是?阿姐替她求的情,这才让凝茂宏松了口。
启程那一日,紫葵偷偷告诉她,息夫人在?自己的院子?里砸碎了好几只瓷瓶,还讽刺她,一个凡体之人也妄想与凝家的嫡小姐争辉,真是?不自量力,惹人发笑。
她笑得眉眼弯弯,根本?不以为意,只觉得息夫人愚昧狭隘。她何曾有过与凝玉娆争辉之心,阿姐在?她心中,本?就?是?整个神都最温柔最可爱的人,生来就?应该拥有世间最好的一切,她怎么可能?会想要?去抢她的东西。
压根没有明白,这分明是?紫葵在?息夫人的授意下,这样旁敲侧击地提醒她注意自己身份,让她认清自己,不要?痴心妄想。
而那时坐在?马车上的她满心欢喜,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的书院,和阿姐要?去的,压根不是?同一个。
随着神都南迁,原本?的五大书院如今已经凋零,只剩下了跟随神都重新落地的辟雍书院,和本?就?位于澜庭江南岸的东序书院和成均书院三所。
阿姐去的,是?在?神都之中赫赫有名,非世家子?不得进,借玄天塔之势,集中了整个大徽朝最顶尖捉妖师与座师们的辟雍书院。
她被送去的,是?如今已经居于最末流,摇摇欲坠,无人问津的东序书院。
或者说,是?她八岁那年坠入的冬日长湖的所在?地,她最恐惧的地方。
那一次的马车坐了多久,凝辛夷已经没有印象,她只记得颠簸摇晃,还?不如此刻的梦境温暖平稳,让她在许多?瞬息之中,明明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却依然不愿醒来。
梦境变得破碎虚幻,也许是身体感受到了太过久违的温暖,让她的梦飘去了另外的画面中。
从东序学院的长湖中被捞起来后,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极度畏寒,沐浴时要最热的水,皮肉都变得通红,她才能感觉到一点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