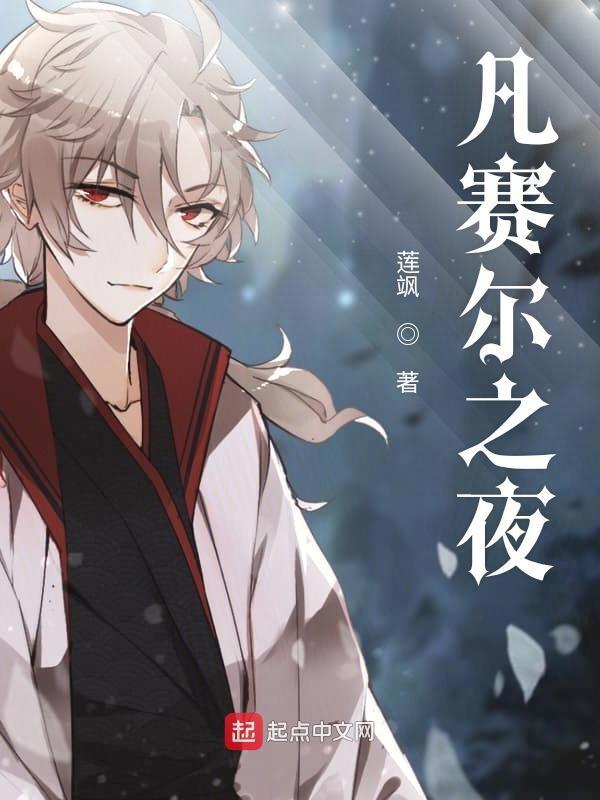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落日陷阱by砂梨免费阅读 > 第156节(第1页)
第156节(第1页)
他的大脑逐渐淡化了这件事。
经徐叔那么一提醒,孟鹤鸣像被打通了四肢百骸似的,有股说不清的热潮顺着血液横冲直撞。
常年四平八稳,他都快忘了被热忱冲昏了头是什么滋味。现在心里轰轰隆隆,几百台大型机械同时开工都没他心口那么喧嚣。在光亮的电梯壁里看到自己露出青灰的下颌,他终于感觉到神思回到了现实。
按亮开门键,从容不迫地迈了出去。
这个点央仪已经睡了。
客厅拉了一层白纱窗帘,花园灯透进来些许微光,配合柜面下的感应光带,能勉强看清屋里的陈设——沙发上放了几本画册,矮几上有一杯未喝完的牛奶。路过墙边垃圾桶时,桶盖感应到人声,自动开了。
他瞥一眼,看到几张撕碎了的纸。
孟鹤鸣停了停脚步,从旁离开。
几步之后他又折回,目光幽深地落在敞开的桶盖上。
几分钟后,客卧卫生间响起簌簌水声。
男人慢条斯理地洗干净手,又拿了衣服就地冲了个澡,等一切都做完,轻手轻脚推开主卧的门。
床上央仪睡得正熟,以一个保护性的姿势向左微微侧卧,腰下还垫着一个软枕。她平时睡觉就乖,特别是累极了,一沾枕头就能睡着,中途连姿势都不怎么换。
孟鹤鸣放轻脚步,在她空出的另半边坐下,手指控制不住地碰了碰她的脸颊。
羽毛般轻柔的一下,她却眼皮抖动。
过了会儿,迷迷糊糊抬眼:“……嗯?谁。”
“我回来了。”他低声。
睡的朦朦胧胧,大约早忘了他还有三个国家要飞,央仪抱紧被子点了下头:“嗯。”
这声之后没了声音,看来是又睡着了。
孟鹤鸣没再扰她,在一旁躺下。
连日繁忙让他也睡得很快,再次醒来是早上,没来得及看几点,就发现一双干净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看。他伸手,揉了揉对方的头发:“醒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央仪半跪在床上,迷惑地看着他。
闻言,他笑了声:“昨晚上我还以为你被我弄醒了。”
央仪摇摇头:“毫无印象。”
前几天起她总觉得自己反应有些钝,干什么都心不在焉的。直到经期忽然延迟,她猛地就想到了什么似的心口一跳。
这半年不是没闹过乌龙,于是她第一时间想的是自己偷偷摸摸去医院查。
检验单子就在床头柜里。
两次检查中间隔了一天,hcg翻倍良好。
但这个好消息,目前连李茹都不知道。
央仪抿住唇,心思又飘摇起来。是一会儿直接拿给他看?还是找个特别的时机?
要怎么说?
——孟鹤鸣,我怀孕了。
平铺直叙毫无感情,pass。
——那个,你要当爸爸了。
不行,太普通太没有创意,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