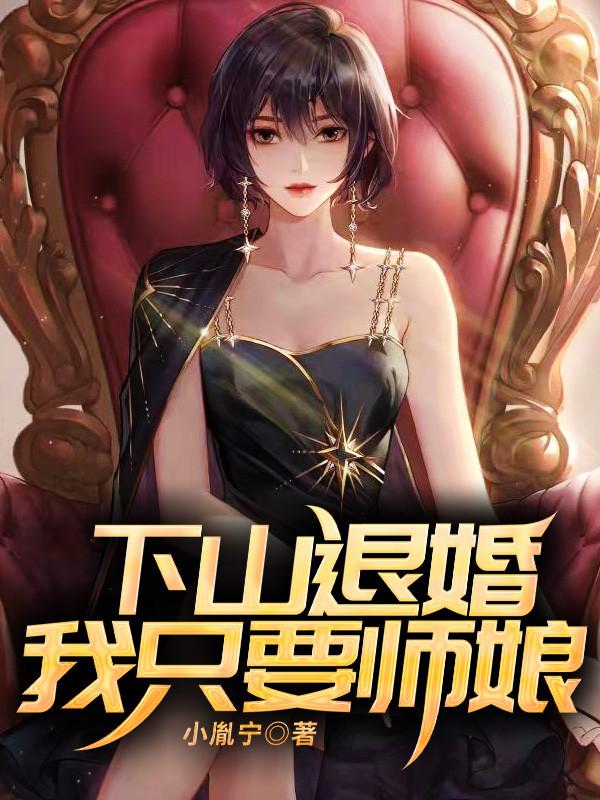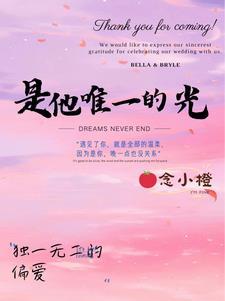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九案侦办组红安 > 第17节(第3页)
第17节(第3页)
三、就是当地人
从芳城走后,九案侦办组直奔祥县。
这个案子的破案条件最好,有足迹,有指纹,有DNA,而且与六年前发案时相比,城乡改造变化不大。
上一次来,朱会磊回北湖去做芳城的检材了。所以,这次关鹤鸣说:“小朱,上次我们去过现场,你没在。咱们明天一早出发,再去看看。”
他的记忆力好,方向感强,下了车就走在前头,大步流星。
朱会磊紧紧地跟在他身后,从坡上下沟,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松软的黄土和垃圾,黑色的皮面运动鞋上马上就覆盖了一层土。
走过小河沟,关鹤鸣说:“孩子们就是从这儿被带走的。有两个孩子的袜子,案发第二天被发现在沟里漂着,一个孩子的袜子装在兜里。三个孩子为什么光着脚穿鞋走路呢?”
朱会磊想也没想,就说:“三个孩子怕把袜子弄湿,就脱在岸边了。遇到突发情况,他们来不及穿袜子就走了。第二天,袜子被吹到了河沟里。所以,应该是胁迫上坡。”
“这个人可能手里有个什么厉害的东西,孩子们很害怕,慌慌张张地就跟着上坡了。”关鹤鸣说着,忽然看到罗牧青眼睛里写着“不信”两个字,这是“老刑侦”一眼就能看破的。
“小罗,你认为呢?”他问道。
罗牧青被点名,脸一红。她知道,自己如果说出不同的想法,一是会惹怒领导,二是会被人嘲笑。但她又觉得,既然被看穿了,不说才是矫情,于是便故作镇静地说了出来:“我记得案发的窑洞里有一瓶大蝌蚪,据说这条河沟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有可能是案犯从别处捉完蝌蚪,走到这条河沟边,正巧碰上三个女孩,告诉她们翻过土坡有条河可以捉到大蝌蚪。于是,三个孩子就争先恐后地跟他走。”
“哟,你这想象力还真够丰富的!”朱会磊故意走到她身边,小声地说。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过。有可能是案犯偶遇三个女孩,引诱她们上山。但是仔细分析,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大蝌蚪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关鹤鸣接着说。
“为什么不可能?”罗牧青追问道。
“离这里最近的河沟也要走上半小时。三个孩子都是土生土长,最大的十一岁,说翻过土坡就有河沟,她们不一定信。另外,从当天的足迹照片看,虽然足印重叠,但始终成一行排列,一点儿不乱,说明三个孩子是排着队的。如果是争先恐后,足迹肯定会乱。”关鹤鸣解释道。
这一番话让罗牧青真切地感受到,关鹤鸣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得出这样严密的推理结果的。
通往土坡的路竟变成了工地。祥县公安局局长魏可光说:“这儿要建一个绿林公园,上次你们走后就开工了。”
这个工地并没有扰乱关鹤鸣的方向感,他的脚步丝毫没有减慢,顺利地从工地穿出去,来到了土坡近前。沿着犯罪嫌疑人带着孩子们走过的路径,他很快就看到了山坡上的几座废弃的窑洞。
关鹤鸣指着不远处的窑洞对朱会磊说:“在小河沟那边能隐约看见一片土坡,但看不见窑洞,可案犯却带着三个小女孩直奔这边来了。”
朱会磊说:“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对这里比较熟悉,知道这里的土坡上会有废弃的窑洞。”
关鹤鸣笑而不语。进了案发的窑洞,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自言自语:“东西两个窑洞,中间有个过道厅,紧里边还有个小窑。”
小窑矮,面积也小,大概就五六平方米。关鹤鸣先进去,邱实打开手电筒紧随其后。朱会磊个儿高,背不由得驼了起来。
罗牧青站在小窑门口,眼睛一直盯着窑壁看。一只只大黑盖子虫还在窑顶上趴着,灯光一照,纷纷爬动起来。她后背发凉,头皮发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难道他们都没看见吗?”她暗想。
“尸体全都移到这儿了,门口还挡了枣刺。”关鹤鸣说。
“枣刺是什么?”朱会磊问。
“就是当地的一种植物,每根枝上都带好多刺,当地人叫‘枣刺’。”邱实解释道,朱会磊点了点头。
从小窑出来,往外边走,经过中窑过道,关鹤鸣说:“从这儿提取到了两个烟头,‘黄山’牌的,当时大概五块钱一包。”
出了窑洞,太阳正在一点点地升上高空。他们一起往坡上走。罗牧青的鞋里灌了不少土,走到坡顶,她知道其实每个人的鞋里都是如此。但是,好像没有人介意。自然,她根本来不及脱下鞋把土倒干净,关鹤鸣不会给她这个时间。
他们急匆匆地回到住处,回房间洗手、换衣服和鞋,一刻钟后一起吃饭。
关鹤鸣看着身穿运动服、运动鞋,还随身带着笔记本的罗牧青,心里暗自发笑:这个记者适应得挺快,这回全是运动装,随时准备出发一样。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