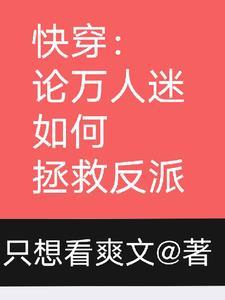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娑婆诃是什么意思 > 第6章 6(第2页)
第6章 6(第2页)
俩人都犹疑着不动。
片刻后,提灯先起身:“那就有劳了。”黑衣人方跟上。
一路走,姜昌找话说着:“看你们拿了包袱,是出远门的?原要去哪?”
“原就是来须臾城。”提灯接话道。
姜昌走在他们前面,只一个徐徐前行的背影:“那可巧,来须臾城做什么?”
“找人。”
“找谁?”
姜昌问出口,半晌没得回声,才察觉自己问多了些,正回头要向提灯解释:“我只是……”
却见提灯斜眼看着后方不紧不慢跟着的那人,似是在等对方说话。
“你不用等他说话。”姜昌慢下来,与提灯并行道,“这公子只怕是个聋哑。我才救起他时,问什么也不说,也不晓得听没听懂。应是迫于无处可去,才一直守在那儿跟我回来。”
提灯收了眼神,看似不经意道:“是么。”
行至姜昌家中,天已擦黑。
这是一处瓦舍,说不上富丽堂皇,却也收拾得干净敞亮。
屋外一个栅栏围起来的小院,一侧安置鸡笼,里头喂了几只鸡,另一侧则是菜圃,坝子里一堆焦木,当是前一晚燃尽还没收拾的。
他们被迎进去,堂屋左边是灶房,右边两间相邻的屋子,都锁着门。
姜昌开了靠院子那间:“你们就住这儿吧。”
遂一面领着人进去,一面开窗通风,到处收拾:“家里原有三间屋子,灶房后那间是我阿妹的,委屈你们挤一处。家中不来客,我时常打扫着,现下倒也还能下脚。你们等等,我去抱两床被褥。”
他一通倒腾,也不叫旁边俩人帮手,自顾快步出去,留提灯和那黑衣男子在房。
屋里一下就安静起来。
提灯抱着包袱,仰头盯着帽檐下的阴影,一声不吭。
对方被他看得不自在,刚侧身想躲,提灯二话不说把步子一挪,又站在那人面前,还打量着看。
两个人浑身湿透,提灯一张脸冻得青白,湿法贴在脖子和后背衣裳,饶是落魄,眼神依旧凌厉不减。
他刚要开口,姜昌又从外头抱了几床被褥进来:“还愣着干什么?瞧这一身湿的,地上都是水。外头院子生了火,还不紧着去烤烤。这两日才开春呢,也不怕冻着。”
说着,把被褥往床上一扔,顺手在地上铺了草席,连连推着两个人往外走:“去烤烤火,快去。”
提灯到了门槛处,瞧见院子中那团熊熊的火,迟迟不迈步。
披风下的人才一抬脚,见提灯不动,又把腿收回去,默默转头看着他。
提灯什么话都不说,只一味凝视那团火出神,又听里间姜昌声音传出来:“怎么了?怎么不出去?”
这才跨出门槛去了。
即便去了,他也只坐在屋檐下,勉强到那火惹出的光晕边沿,便再不肯往前挪。
黑衣人见他坐定,也闷声守在他后头不过去。
姜昌出来见这二人搁火堆坐得老远,一跺脚:“嗐!坐那么远,哪能将身上烤干?我看这柴火干了你俩衣服也干不了。”
说话间就拉着提灯靠近火堆,还有半丈远的距离,提灯说什么也不动了。
姜昌无法,只得将就他。
三人围着火堆坐下,提灯一边拆包袱,一遍跟姜昌搭话:“你阿妹不出来?”
姜昌拿着木棍戳他早前埋在火堆下的地瓜土豆,一张脸由火光映得红灿灿的:“姑娘家,哪能随便出门的。一会儿我给她送吃的进去就成。待会儿我支个架子,你俩把外头衣服脱了,趁火不那么旺的时候放上去烘一下。”又冲对面道:“都到这儿了,帽子放下吧!不然头发怎么干呢?”
提灯正把包袱里的那盏八角灯拿出来,听见这话,也顺势往一边看过去。
那人仍旧不动弹。
“罢了。”姜昌笑笑,“难不难受,还用旁人操心么。”
他收了视线,瞥见提灯从包袱里扯出一块深色布料,像是什么衣裳,可又没全拿出来,只抓着一点衣袖的边角搭在手心伸出去烤,其余还藏在怀里。
“你这得烤到何年何月?”姜昌以为是包袱里头是衣料太过大件,惹提灯不便宜,便欲起身,“我马上拿竹架来,你把包里的衣裳晾架子上。”
提灯道:“不用。”
又说:“我就这么烤。”
姜昌才离了凳子,见提灯不似假意推脱,复坐下:“要这么烤,我看三更方能烤完。”
提灯听他打趣,便也扬了扬唇:“那我就烤到三更。”
柴火底下传出香味,姜昌将土豆地瓜扒出来,撵几个到提灯脚边,又不停换手捧着扔到对面:“今天匆忙,没什么可吃,你们填填肚子。明天杀鸡。”
提灯看着地上的土豆:“你家鸡都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