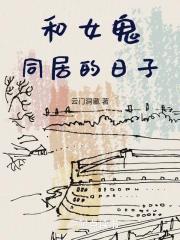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金雀钗玉搔头 > 第109章(第1页)
第109章(第1页)
她浅笑默然了一会儿,竟是没有回绝。
“好。”
“你不是还想要习箭术吗?现在开始学也不晚的。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得寻一个靠谱的师父亲身教着。”
纪野此刻正盯着沈洲的表情,内心暗爽不已,继而扬声说:“邢大人今日箭术大比拔得头筹,正好可以当你的箭术老师。”
和离不过十日,太后便给沈洲寻了世家女子给他相看,所以纪野觉得宋南枝此刻哪怕相看十个也根本没什么的。
沈洲目光一直望向这边,眼尾压着,带着厉色。
太子自然瞥见了他的表情,也知道他肯定也听见了,轻咳两声给了纪野一个眼神,要她悠着点。
纪野偏不,还道:“既然已经和离,便是婚嫁行事各不相干,寻个箭术师父又有什么过分的?”
然后转头问宋南枝:“你觉得如何?”
宋南枝微微颔首。学箭术自然得寻个擅于此道的,才能少走些弯路。
邢祁见此顿时面红耳热,自也不敢推辞,只拱手道:“下官箭术不精,不敢称师父,若姑娘想学,下官定然尽心相教。”
两人互相望了一眼,都浅浅点了头,也算互相打了招呼。
只是这般说完,邢祁莫名感觉后脖颈绕了一阵寒意。他没看见那左侧坐席的人眸中凝起的阴沉,只当是这山林间夜风沁寒。他敬完酒便退回了自己的席座,并不敢当真留下,然后有意无意的会往宋南枝的方向瞧。
因并不知适才见过的姑娘是哪一家的,遂多了些好奇。
这番情景教沈洲看在眼里,他淡然端起的酒杯仰头而尽,随即口中尽是酸涩。
月行中天,乐宴便已过大半。
沈洲望着那两人的空位,手里的空酒杯,在碎与不碎之间来回揉捏。他知道宋南枝适才的答应并不是假话,可他不知道她是当真起了心要习箭术,还是别的什么。总之那句“好”让他十分不愿意听见。
心中不安也逐渐放大,滋生,那手中的瓷杯捏了没几个来回,便起身朝宣帝告退。因为明日回宫,沈洲作为护送自是要处理好猎场余下诸事,宣帝也没拦着他。
猎场护卫一事沈洲早就安排妥当了,遂离开席间便朝营帐去。
因为明日要回京,宋南枝便提前离开了宴席,纪野见此便让邢祁送一送,要两人再认识认识。
宋南枝看着身后跟过来的人,顿了顿步子,先开口道:“我二叔与邢大人曾是同僚,想必邢大人也该知道我是谁了。”
纪野方才在席间故意不告诉他自己是谁,想必是怕把人吓走了。大抵是因为和离的女子多少都会不受人待见,别说相看,就是光聊天恐怕都会有几分避嫌。宋南枝不想让人误会,遂很直白的告知他。
邢祁怔了一下,面上除了有些意外并没有任何要避嫌的意思,反而笑道:“原来是宋大人的侄女。”
宋南枝的二叔与他同府衙为官多年,邢祁是极其了解他为人的。也可以说整个宋家他都知晓,皆是清廉正直之辈,遂不敢有半分的失礼,朝她一揖:“在下邢祁,见过宋姑娘。”
宋南枝亦屈膝回礼:“邢大人可以不用将纪良娣的话放在心上。”
邢祁看她有意回避自己,赶忙道:“无妨,宋姑娘若真想习箭术,也不嫌弃在下笨拙,自然倾囊相授。”
顿了顿,又道:“国子监祭酒是在下兄长,听闻宋姑娘的两个兄弟都在国子监,若是方便,宋姑娘可以来国子监寻在下。”
宋南枝没有想到面前这人竟然是邢逸的弟弟,浅笑垂眸:“多谢。”
两人话说到此也没再往下,邢祁也怕唐突了人,便提前走了。
宋南枝本是要回营帐的,只是适才在席间喝了一杯酒,她想吹吹风散些酒意,便让春杪回去收拾东西,自己坐在营帐外河边小土丘的树底下。
正想清静清静,不料又遇见躲着司夫人的司锦,原是司夫人又说了好些话吓她,又开始在哭鼻子。
宋南枝安慰了她好一阵,见她眼泪停了,方才问:“女儿家大了总算要嫁人的,你便这么怕瑞王世子吗?”
司锦抽泣着说:“我不想嫁人,我谁也不想嫁。”
在宋南枝的印象里,兵部尚书司大人与司夫人伉俪情深,怎么身边女儿这么恐惧嫁人呢?
司锦抽着声又道:“我从小喜欢骑射,娘却不让碰,她只顾着让我千万别留疤痕,因为有疤痕就嫁不出去。可是姐姐从小听话,如她所愿嫁了户部的谢家,可谢家他们一点也不体贴心疼姐姐,纳了妾室,让怀孕五月的姐姐伤心难过最后落了产。谢家出事后,谢府要我爹上御前向圣上求情,我爹没答应,他们便把姐姐给休了,姐姐如今抑郁家中婚姻处处是束缚,我宁愿孤独到老,也不要如此。”
谢荣唯有一个独苗儿子,刚及冠不知如何体贴人,是以嫁进去的新妇让谢夫人一直管压着,后来谢荣犯了事死在诏狱,谢夫人便做主休了儿媳。
宋南枝听见这些话后,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劝了,只摸了摸司锦的头。
司锦看着眼前的人,小声问了一句:“我能问问南枝姐姐为什么会和世子和离?”
宋南枝愣了一下,她与司锦不过也才认识三日,因为两人比较尴尬的身份,故而一直没有告诉她自己的名字,没有想到司锦早就已经知道了。
她坦然回了一句:“只是不合适罢了。”
“不合适就可和离,若我姐姐当时也能像你一样,兴许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