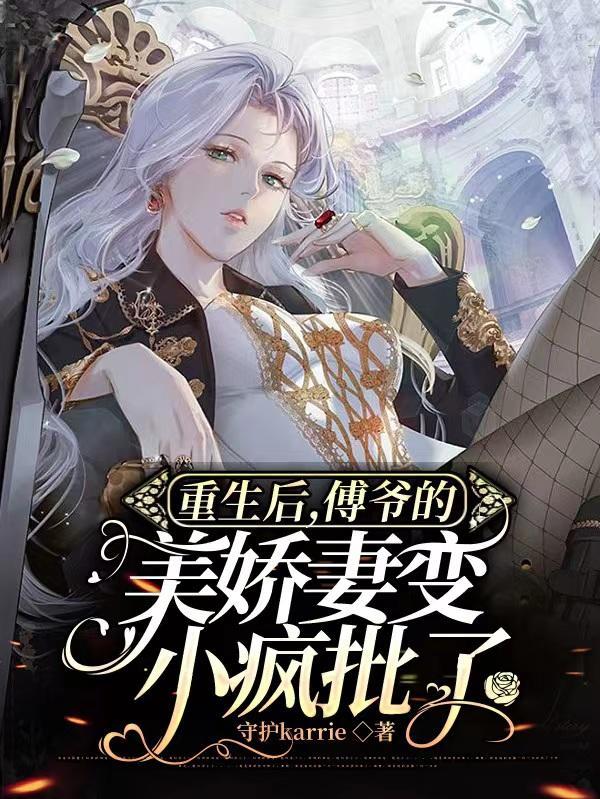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皇朝的另一本秘史阅读 > 第7章 谁说女儿不如男上(第2页)
第7章 谁说女儿不如男上(第2页)
很多年以后王嗣璁从被自己收服的石嫣鹰得到了她初战的真实过程,更是证实了他当年的猜想,将重兵聚集成一团在军事上是很傻的行为,那日与石嫣鹰所率部交战的乃是三万特勤骑兵的前锋部队,大约有五千人。
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在己方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和农耕民族掰手腕,依仗的就是胯下骏马带来的高机动性,对于农耕民族军队来说一人一马就算是精锐了,游牧民族却能做到一人三骑甚至五骑,而且秋冬时节的草原因为温度的缘故地面不会有什么植被,草原也没有山峦之类能够限制骑兵机动能力的地形,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以五千兵力正面击败同等数量的敌军,显然很困难,但石嫣鹰做到了,斩杀与俘虏特勤部骑兵七百有余。
游牧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生产方式,人口承载力很低,另一个地球上的蒙古国,哪怕有着现代技术的加持,196o年的时候人口也没有突破百万,游牧民族的军队是不能和农耕民族的军队玩对子游戏的,哪怕是一换五都是亏。
特勤的五千先锋也不是全都聚在一起,先锋大将派出了多支小规模斥候,对战场迷雾进行祛除。
真实的战争,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战争,可不像RTs游戏,会给主将一个显示屏,将对垒双方的信息都呈现在上面,感知战场的唯一手段就是派出侦察兵进行实地侦查,放出去的侦察兵可能会因为怕死就编造情报回来领赏,因此从来都不是一个一个派出,而是一群一群,既有壮胆也有监视的意思。
有时候,斥候就算尽职尽责也不一定能带回最精确的情报,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对方的数量,俗话说人上一千,无边无沿,很难得出正确的数字,传回去的敌人一千和敌人三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情报还有滞后性,前无线电时代,如果是远距离的侦查任务带来的情报,哪怕是时间最短的,等送到将军手里的时候基本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就算斥候估计的敌军数量是对的,能保证敌军不转向不分兵?
军事主官只能从这些存在极大误差,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情报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来做判断。
百分百准的,那是上帝视角,不是上帝就别要求这个,战争获胜的一方从来都是犯错误最少的一方。
斥候不管回不回来,都会带来情报,不回来就意味着他们战死了或是被俘虏了,就意味着这个方向上的敌人要么有质量优势要么有数量优势,要么两者皆有,特勤的先锋大将现派往东南方向进行侦查的斥候返回的频率显着低于其他七个方向,就猜到东南方向有夏军主力。
先锋未战先怯乃是兵家大忌,特勤的先锋大将立刻点将布阵,留下必要的驻守营地兵力后,就领着两千精锐朝东南方向进军,打得算盘就是赢不了也能跑得了,游牧民族的性格特点就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两千特勤骑兵遇到了石嫣鹰率领的五千夏军,现兵力差距过大,特勤的先锋大将二话不说就要撤退,夏军在追击的过程中杀了将近四百名特勤骑兵,加上之前击杀的斥候小分队,累计斩杀七百余。
特勤先锋大将带着大部分将士回到营地后,二话不说就朝着缀在正北二百里处的本阵前进,本阵得了战报后决心撤退,游牧文明军队对农耕文明军队的战法基本上都是利用机动性拉长对方的补给线,对付草原民族最难的地方就是找到他们,冠军侯霍去病屡屡能找到匈奴主力,就是因为他的军队中有大量的匈奴带路党,这些人熟悉草原的地理,知道哪里有水草,哪里适合扎营。
这就是五千打败三万的真相!算是石横天给女儿石嫣鹰的造势。
同时为了提高此战的含金量,捷报上还刻意注明朝廷天兵击溃的乃是特勤部最为剽悍的狼牙铁骑,实际上游牧民族的生产力非常的拉胯,普通士兵有个皮甲就不错了,不少部族因为炎黄农耕王朝的铁器限制输出政策搞得连金属箭头都没有,只能用骨质箭头,这种箭头射在金属铠甲上的唯一结果就是碎裂。
狼牙铁骑那是特勤王庭的核心战力,哪会轻易用在侦查上!
以上就是针对原文第五十四章中的“先,两个人成名的时间基本相近。石嫣鹰成名的时候是在十八岁那一年,指挥一支五千人的小股骑兵击败特勤人剽悍的狼牙铁骑三万人”这段文字基于冷兵器时代逻辑的冰冷演绎。
但不能因为战报注水就否定石嫣鹰的军事才能,王嗣璁上辈子所生活的中文网络社区有这么一句话:战报会撒谎但战线不会,典型例子就是二战时期的日本与果脯,一个海战大捷不断,美国海军的企业号航母在日本的捷报中被击沉了四次,最后却是东京湾无条件投降,另一个则是歼敌一个亿,最后虎踞福摩萨。
在没有王嗣璁的世界线上,石嫣鹰可是与女一号阴玉凤并称的军事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指挥能力也跟着增长,终于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覆灭了北境三大蛮族之一的赫烈部,将战线一举推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老巢附近!
北狄有三大部族:赫烈、特勤与匈蛮族。
匈蛮可以联想到匈奴,赫烈和特勤,非要穿凿附会的话赫烈对应蒙古的克烈部,特勤是突厥语词汇,是一种官职,多由王子充任,或统兵在外,或奉使外邦,级别仅次于叶护与设。
石嫣鹰覆灭赫烈部之战不是说将赫烈部人杀光了,游牧民族啥不多就是马多,真要是四散逃跑大军根本追不上,石嫣鹰是通过斩的方式对赫烈部的王庭进行了突击,失去了指挥中枢后的赫烈小部族便一哄而散,加入特勤的加入特勤,加入匈蛮的加入匈蛮,草原上并没有羞耻文化,司马迁在史记对匈奴人性格的记载就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王嗣璁能知晓这个消息与他这一世的便宜母亲郜慧彤分不开,她并没有因为生活于深深庭院之中而放弃女将军的梦想,反而一直通过邸报来关注这场生于北疆的战事。
邸报虽然名字中有报,但并非是报纸,最初是地方在京城永安所设办事处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整理,然后通过驿站系统传回各路治所的文抄,到了郑朝时期,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各地驻京办的官员们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
干朝时出现了专门出版邸报的通政司,通政司由于是朝廷机构,其行的邸报相较于民间就成了最权威的文报,通政司也就成了后面朝代的标配机构,需求的上升让邸报也由手抄展到了雕版刻印。
夏朝的通政司会在每月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廿二与廿七这五天出版邸报,每次刊印一百份,送给中央与地方机构,通过邸报可以了解朝堂上的动态与最新的时政,乃是士人群体的必备文书,但一百份的出版量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士人群体的需求,王家印书坊的一大业务就是对邸报进行复刻与整理,但时效性肯定比不上通政司,但封建时代的信息传播度低下,晚一期两期,甚至三五期都不是什么大事,此业务每年都会给王家带来至少十万两银子的纯收益。
郜慧彤显然是有两把刷子的,利用从便宜夫婿那里得来的信息和自己的经历与学识,虽是纸上谈兵但也推算出了这次扫北之师的大概规模,此方炎黄世界也有指导农业生产生活的二十四节气,秋收时节大约在太阴历的秋分前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兵马未动粮秣先行是战争的铁律,经过一个半月的催科与运输,夏廷将筹集来的粮秣送到了北方的前线,大约有六十万斛。
斛是粮食体积单位,换算成公制单位中的重量单位公斤约是六十公斤,一斛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夏廷给与底层兵卒的待遇是一日两升米,这里的米可不是精米而是没有脱壳的稻谷,米去掉稻壳后会有三成的重量损失,能有九百克精米留下。
这是郜慧彤在没有被宗门收入弟子前的农家生活经历告诉她的,郜慧彤幼时做得最多事情就是给家中成员舂米做饭,家中饭量最大之人就是身为农活主力军的父亲,一天大约要吃掉两斤的精米。
两斤精米所提供的能量大约为一万四千千焦的能量,普通人一天所需要摄入的能量约为八千四百千焦,完全足以对付。
其实不然,作为消化器官的胃最怕蛋白质丰富的油水类食物,越吃得油水多越难消化食物,现代人之所以吃得少还感觉不到饿就是因为油水吃得过多,胃再使劲蠕动也无法磨碎食物,食物得不到降解,因此肚子成天都是饱的,所以,天天吃大鱼大肉的人根本就没有食欲,封建时代就不一样了,只能依靠碳水来补充能量,因此人的食量很大,王嗣璁上辈子小时候看过生产队里面的叔伯吃饭,一个人就能将一大盆白米饭或是十七八个馒头吃光,下午干完农活回来还是饿。
一斛粮食省点吃理论上可以供一名士兵食用两个月,六十万斛粮食足以让六十万名士兵维持两个月,但问题来了,六十万斛并非全都是粮食,而是粮秣,粮是人吃的,秣是马吃的,想要与游牧民族作战没有骑兵是不行的。
马按照通途可以分为挽马,驮马与乘马三大类,乘用马是一种很娇贵的动物,单纯吃草根本没有办法养膘,必须喂食燕麦、豆类和米糠之类的饲料,游牧民族之所以多选秋天南下就是因为这个时节的草会结籽,草籽富含蛋白质能起到豆类饲料的作用让胯下的骏马蓄膘。
马的食量远大人类,夏廷兵部规定一匹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换言之一匹马的维持费用能养七个士卒,假设战马与士兵的比例是一比一,那么六十万斛粮食只够六十万骑兵吃七天半。
以上是最最理想的军队在驻地的消耗情况,一旦进入运动战,消耗会更加的巨大,儿时的农活经历,或者说是常识,让郜慧彤知道一个精壮男子不妨碍步行的负重是七十五斤,由于士兵和民夫都属于强体力劳动者,故一人一天吃两升米,75斤米可以让两人吃十五天,加上士兵自带五日口粮,共可支撑十八天,考虑到返程,则前进范围为9天路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二十六天,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三天的路程。
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六天的路程。
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是封建军队的极限了。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驮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
与人工相比,虽然能驮的多,花费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
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军队不可能全部出动,必须留下必要的兵力来守备后方与维系补给线的通畅,只有精锐的机动兵力才能出动,与全民骑兵的游牧民族作战,封建王朝只能派出骑兵,郜慧彤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一次朝廷所出动的军队绝对不会过四万,骑兵不会过一万,而且军事行动时间必然要赶在十一月前结束,因为胡天八月即飞雪,初冬十月还好说,一旦进入十一月就麻烦了,气温下降会导致运输成本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