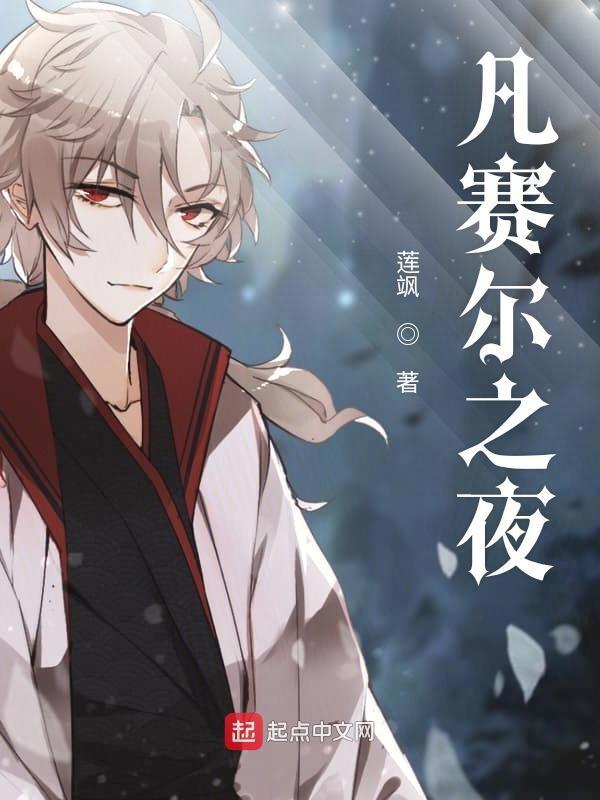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男生穿越到古代的大全集 > 第115章 平凉县主(第1页)
第115章 平凉县主(第1页)
等到了十五这天,每年和他一起逛花灯的齐国安却是写信过来,言辞间皆是歉意。说自己要陪文氏去逛花灯,还要回一趟文家料理琐事,今年就不和他一起逛花灯看鳌山了。
贺景时得了消息,却是喜色难掩。他等宴席散了,便兴冲冲去找了景春。他衣袂带风,面上难掩喜色:“往年你那师父总将你拘在身边,难得今年肯放人。今年可算得了空,定要好好玩一玩!”
他去年就及冠了。他今日特意着了宝青色蜀锦松涛纹刺绣滚边斜领袍,青玉睡莲小冠束,鎏银雕松叶簪斜插其间。腰间的四合玉佩随着步伐轻响,衬得他身姿愈挺拔如松,更显得他丰神俊朗。
景春因尚在守制,衣裳的颜色不能穿的太艳。他一袭蜜合色团花暗纹茧绸曳撒,水青色带松松绾了青丝,双鱼银项圈在颈间泛着微光,褐色祥云丝绦系于腰间。
陈妈妈在一旁细细打量,忙取来一顶大帽替他戴上,又将月白色菱花大氅交给丰年,千叮万嘱道:“路上人多热闹,哥儿若是热了就把大氅脱了;等花灯散了,夜深风凉,可一定要记得披上,仔细着了凉。”
贺景时笑着招呼景春等人上了马车,一边整理着衣袖,一边说道:“今年大鳌山设在国安寺前的大空地上,离咱们这茱萸胡同远着呢,坐车去才稳妥。”
景春微微叹气:又要坐车。
说罢,贺二夫人、贺三夫人各携着几个小辈,分乘三辆马车,一众家丁婆子前呼后拥,往花灯盛会去了。
街市上早已是花灯如昼,火树银花。一盏盏造型各异的花灯与往年并无二致,可贺景春望着那流转的灯影,心底却空落落的,总像缺了点什么,兴致始终提不起来。
但他素来心思细腻,不愿扫了大家的兴,面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意,与贺景时等人谈天说地,时不时还开上一两句玩笑,将自己的失落藏得严严实实。
待至国安寺前,只见人山人海,寺前灯火通明如白昼,周遭树上挂满了各色花灯与灯谜。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卖糖画咯,栩栩如生的糖画!”“桂花糕,香甜软糯的桂花糕!”
伴随着爆竹烟花腾空绽放,“噼里啪啦”的声响与人群的欢笑声混作一团,十分热闹。
贺景时迫不及待的带着几个弟弟妹妹去猜灯谜去了。笑声、闹声混作一团。
过了些时辰,众人得知大鳌山尚需些时候才点灯,大家便各自分开,先去别处玩了。
景春知道国安寺的后山里有许多草药,早就想来挖一挖了。他便和贺三夫人说一声,带着丰穗和丰年去了国安寺里。
一进寺内,香烟袅袅,满殿灯火将佛像映照得庄严肃穆,与外面的喧嚣热闹仿若两个世界。贺景春在佛前为母亲上香,神色虔诚,三拜九叩后,久久未起。
丰年见四下无人,便凑到景春耳边,压低声音道:“三少爷,咱们何时动手?”
景春仍跪着,嘴唇微动,喃喃道:“明日。”
不多时,外面的夫人、小姐们陆续进殿祈福,殿内渐渐热闹起来。贺景春这才缓缓起身,带着丰穗丰年往后山走去。
后山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远处零星的几点灯火,仿若鬼火一般。积雪覆盖在地上,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
景春提着灯笼,深一脚浅一脚地寻觅着,无奈积雪太厚,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
丰年知道景春出去外面总会有摘草药的习惯。可他看着黑漆漆的四周,有些担心道:“三少爷,不然咱们还是等白天再过来吧。”
景春摆摆手:“外面闹哄哄的,我才不去。等大鳌山点灯,钟声一响,敲钟后咱们再去也不迟,跟着大鳌山一路走回去就是了。你和丰穗若是待不住了,便自去玩吧。”
丰穗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还真的不客气的走了:“三少爷,我去瞧瞧庙会的点心,买些带回去给点心铺子做个样子,说不定还能琢磨出些新花样呢!”说罢,脚底抹油般跑开了。
丰年气的牙齿在咯吱咯吱响,一旁的景春有些好奇,这天寒地冻的还有耗子?却也拿了银钱给他:“既如此就多买点,你也给丰年买一些,回去再一起吃。”
丰穗这厮高高兴兴的走了,忽略了丰年那要吃人的目光,大声喊道:“三少爷要等我啊!”
丰年翻了白眼。这人不好好在主子身边跟着,就知道跑去玩。
好半晌才一拍脑门,懊恼道:“哎呀,我竟忘了!这大雪覆盖,哪还有草药可采。你瞅瞅我这脑子,真是糊涂了。我还在想是不是要把雪挖出来再采。”
丰年一脸恍然大悟:“噢”
两人笑了一阵子,便慢悠悠地往回走。
景春边走边和丰年庆幸道:“幸亏师父不在我身边,不然知道了可不得打死我。你可不知道,他平日看起来一副好说话的样子,一说起草药,那可凶得很,训起人来毫不留情,我从小就没少挨他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