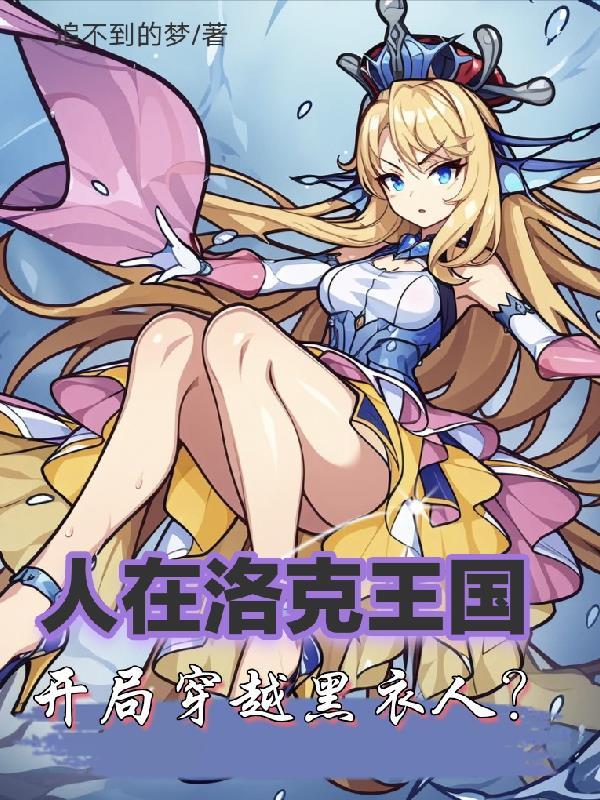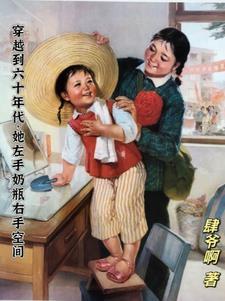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2020年女生宿舍 > 第26章 有趣的人 new(第1页)
第26章 有趣的人 new(第1页)
黄彦彦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人。只不过特别喜欢流眼泪。
桑桑第一次跟他在后台聊,现他很有钱,就有点自卑。桑桑倒不缺钱,只不过她开销的,都是乡里和寺里的钱,因此,她平日里一直省着花。
但黄彦彦似乎很能和她共情。这一点其实很怪。他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吗?
桑桑还记得,黄彦彦第一句触动自己的话。
“桑桑,你知道吗?不光是你,这个世界,穷人很多的。他们自己也不想当穷人啊。但是没办法。”
“你信不信,就是现在,在距离天安门直线五十公里的地方,你都能找到中国最穷的地方。”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录完那一期节目的周末,黄彦彦邀请桑桑一起出了趟北京城,一路往西往北。
可能走了不止五十公里,但也远不了太多。应该是属于河北张家口的地界。
桑桑清楚地记得那条灰突突的国道上,运煤大卡车往来穿梭,扬起的灰尘弥漫四周。
道旁是尽显岁月痕迹的七八十年代砖瓦平房,原本洁白的瓷砖如今已被煤灰染成泥巴色。
就在这破败之中,平房外一块“自助餐,十二元一位。有酒有肉”的牌子显得格外突兀。
初春时节,路边的杨树同样灰突突的,毫无生机,黄彦彦的m3在这条路上行驶了没多久,就蒙上一层灰,亟待清洗。
接着,黄彦彦又把车拐进了一条小路。小路的尽头也不知道是哪里,但黄彦彦明显是来过的。小路越开越窄,最后拐进了一个小村庄。
这里,莫不是就是黄彦彦说的,中国最穷的地方了?
眼前是一个极为贫穷的小村庄,规模极小,屈指可数的几十间房子稀稀拉拉地分布着。
村子里的路窄得可怜,仿佛连一辆小型车辆都难以顺畅通过,勉强能容两辆电瓶车擦身而过。
所有房屋皆是土坯搭建而成,岁月的痕迹在它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屋顶的状况也是参差不齐,有的铺着破旧的瓦片,那些瓦片缺角少棱,像是被无数次风雨侵袭后留下的残痕;有的则仅仅覆盖着一层茅草,枯黄的茅草在风中瑟瑟抖,仿佛随时都会被吹落;更有甚者,一些屋顶已然坍塌,黑洞洞的窟窿像是一张张绝望的嘴,诉说着生活的艰辛。
放眼望去,整个村庄毫无一丝绿色,仿佛这里是被大自然遗忘的角落,除了泥土那单调的土黄色,竟找不出一点其他颜色。
世界仿佛被抽去了色彩,只剩下一片荒芜。
车辆艰难地拐过一个弯,眼前终于出现了一抹不同的色彩,那是一堆藏青和黑色。
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群人。
他们身着的军大衣,款式陈旧得仿佛是从抗战片里穿越而来,颜色暗沉,布料粗糙。
有男有女,大概七八个人,毫无秩序地堆叠在一起,相互挤靠着取暖,就那么睡在户外路边的一块破旧的匾上。
当慢慢走近,便能看清他们的面容。
这帮人年纪其实不算大,大概四五十岁到五六十岁的样子,可岁月却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让他们显得格外沧桑。
此时,在这初春的暖阳下,他们却都一动不动,仿佛时间都在他们身上凝固了,整个场景弥漫着一种令人心酸的死寂与疲惫。
桑桑突然也很心酸。经年累月的贫穷,让这些人的时间变得毫无价值。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晒太阳,但其实,只是在等死而已。
这里比自己的家乡更穷,因为它的人民已经了无希望。
“我曾经在这里支过教,但后来,”黄彦彦说着,转过头来,然后桑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这里小孩没有了,年轻人也没有了。”
桑桑不解,她歪着头问:“为什么?”
黄彦彦又转过头来,盯着她,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共同富裕。”
那天晚上,两个人住在附近的某一家小县城里。
小县城里,别说万豪,希尔顿,洲际,连如家和汉庭都没有。
黄彦彦在携程上挑了一家看起来不错的,已经属于县城最贵的酒店,定了2个大床房,每间才9o元一晚。
到了酒店,两人才知道为什么这家酒店这么便宜。
酒店里面倒是新装修,拾掇得还有点快捷酒店的样子,家具都是仿宜家风格的。
但酒店外,整条马路都被翻修得尘土飞扬,也不知道是要扩车道还是铺设水管。
而两条大马路交汇的十字路口,都用蓝色铁皮墙高高密密地封着,想走到马路对面去,根本不可能。
黄彦彦拉着桑桑,本来是看大众点评,要去对面吃饭的,此刻也只能折返,在酒店后面的这一条小街上找吃的。
而这一条街,在大众点评上,搜不到任何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