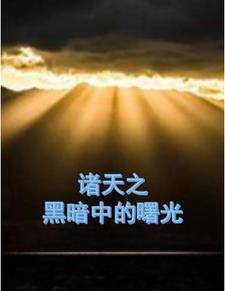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解梦无限by榆鱼晋江 > 第九十五章(第2页)
第九十五章(第2页)
每次补课结束,林随意会去送送家教。
主要是好奇楼唳的水平。
听到家教说楼唳没问题,林随意才咧开嘴笑。
他也算终于理解到元以对自己的心情了,他风光,元以也风光。
楼唳虽然是他的编外弟子,也算半个弟子,楼唳学业没问题,林随意也才能没问题。
距离开学的这十几天里,林随意还折返回去了一趟元清观,他做下的这个决定还是得禀告元以。
元以刚解了梦魇之梦,受梦主情绪影响,精神气不太好,林随意也不敢说多了,只向元以保证,他是决定要帮楼唳,但不会试图更改楼唳的命运,情劫也一定会解,但是要等那个告诉他谁是系铃人的人出现。
他还对元以说,他虽然不常在元清观,但他依旧是元清观的人,他会继续为人解惑消灾。
元以摇了摇手,知晓林随意做了决定便再难更改,只叹气道:“元意啊,想得太简单了。”
林随意不想和元以辩证什么,他站在台阶上看着元以,身后有一颗桃树,树上结着果,大都熟透了。
“师父,一切后果,我自会承担。”
元以挥手不欲再说,林随意拱手,转身离开。
他看着林随意的背影,树上一颗熟透了的桃子砸下来,摔在地上,果肉泥碾。
很多时候,元以回想这日,他悔于放林随意离开,他应该……
应该死死地拽着林随意,软磨也好硬泡也罢,哪怕是哭天喊地都应该把林随意拦下来。
应该把林随意拦下来的。
-
林随意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行踪,一些上门请他解梦的人不再去元清观,而是辗转到这里。
在楼唳开学前,楼唳就见到一次单主上门请林随意解梦。
一个西装革履的国字脸,还带着他的司机。
二人风尘仆仆,看起来是从很远的地方找来。
楼唳提前把桌子上的书本收了,抱着酒店里准备的白色大瓷杯沏了三杯茶。一杯林随意的,另外两杯是给那二人准备的。
他自己没有,他就站在林随意身边,座下童子一般安静地听。
“元意道长。”
国字脸一进门,差点扑倒在林随意脚边,还是司机搀扶着才勉强坐在椅子上:“求您救命。”
林随意问他:“梦了什么?又一连梦了多少日?”
“我梦见我采了很多菊花,我把菊花摆在家里。”国字脸恐惧地回答:“这样的梦连续一个礼拜了!”
“梦菊,梦菊大多是吉,菊寓意收获,梦赏菊、采菊、赠或得菊都可寓意心愿可成。”林随意又问:“不过要区别到底是吉梦还是凶梦要看你具体梦了什么颜色的菊?除此之外,你在梦里又做了些什么?”
国字脸脸色发绀,颤抖着回忆梦境:“我梦见我的家里被我摆满了菊花,满满当当的,到处都是,就像……就像灵堂一样,我就在花丛里……”
“菊从哪里来?”林随意问。
国字脸追忆道:“好似是我采摘而来的。”猛然想起什么,国字脸嘴唇都白了,“菊花的颜色是白菊……”
“白菊啊。”林随意呢喃一声,低头喝了一口茶水。
国字脸察觉不妙,“元意道长,是不是……是不是……”
楼唳这小子沏茶沏得还不错,林随意一口气喝干了,把杯子交给楼唳,楼唳会意,又给林随意倒了一杯。
这个中途,林随意问:“在梦里采摘的白菊是连着根茎还是单有花朵?”
“好像……有根茎,哦不……没有,不不不……有……没有……”
“你说白菊是你采摘的。”林随意继续细问下去:“在哪里摘的白菊?”
国字脸不敢怠慢,连忙回忆梦境:“我想想……好像是……河边!对,是在河边。”
“河到你家的距离。”
“远!我记得我走了很久很久,走得我都累了。”
“累?”林随意念了一声,笑起来,对国字脸说:“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尽早治疗还有得救。”
国字脸一怔,反应过来后忙不迭点头:“好好好,我这就去。”
林随意:“那就不送了。”
国字脸:“您留步。”
国字脸走后,桌上多了一张支票,林随意拿起看上面的数字。
“楼唳。”林随意唤道:“你解解这梦。”
楼唳哪解得出来,林随意就拿支票敲他脑袋,吐出:“笨。”
他公布答案:“梦金菊是吉,但梦白菊不是。单主梦见白菊本身就不是什么好寓意,再则他提到采摘白菊的河边很远,他走得很累,若梦里行走乏力则预兆肺上有疾,这不是有病是什么。而他之所以还有救,也是因为那条河,他在河边采菊却未沾水,便是‘河’字去三点水只剩一个‘可’,加之梦里他先笑后哭,反解其梦就是现实里先哭后笑,不难得出‘重病可愈’的结论。”
楼唳记下了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