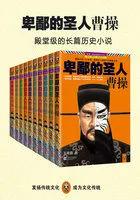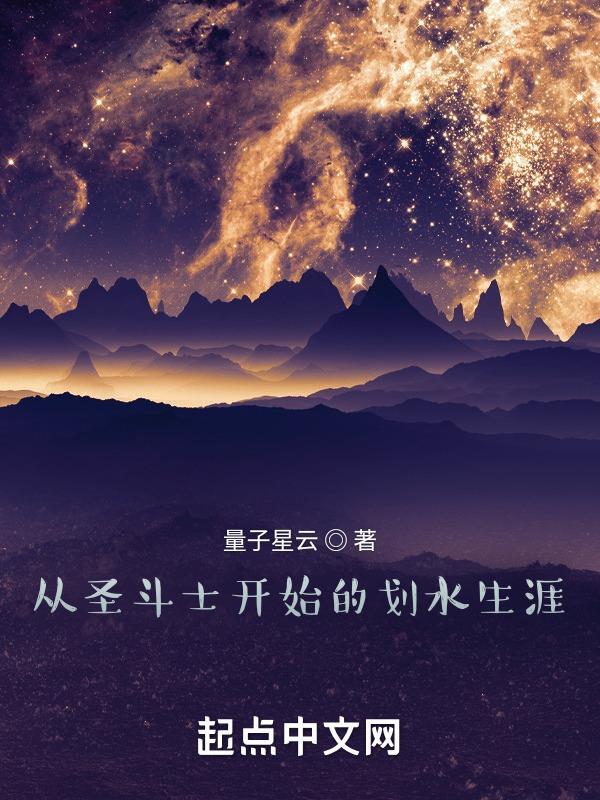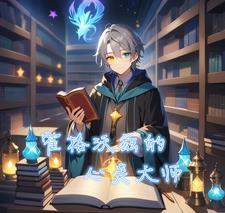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农家幼崽竹马日常TXT > 第87章 条件(第1页)
第87章 条件(第1页)
一说到牛,章小水就敏锐的察觉到崔大郎格外感兴趣。
崔大郎道,“那你们这县令口碑如何?”
章小水道,“咱深山的庄稼户,自然不知道县令大人在城里如何,但是我觉得他是干实事为百姓着想的好官。不仅取消了入城税,还组织牛市控制价格,听说还自费掏钱从别的县买了十几头牛。又考虑到百姓没钱,还以低于市价的息钱给百姓赊钱买牛。”
崔大郎毕竟年轻,也就二十一二岁左右,正是不禁夸的年纪。
他忍下嘴角,端着严肃的疑惑问道,“但据我所知,那低价的牛怎么也还卖不出去,就是上门赊卖三年还清,官方最低月息三分,其他银钱铺子都是四分,那县令自掏腰包给出了两分,就这样低息钱了,一问百姓都连连摆手。”
何止摆手啊,崔大郎下乡进村说起这个事情,没人不骂的,想起这事就怄,又无可奈何。
都说这是贪官污吏想出新的捞钱的法子,还说官府把老百姓当傻子,只想从老百姓身上吃息钱坐着等钱生钱,老百姓才不上当。
还有的是心动,可不会算息钱,就是托了村长算后也忐忑不安,怀疑官府说好的三年还清,要是中途变卦要他们提前还,那不得把他们折腾的家破人亡了?
老百姓忐忑顾虑重重,给信心满满的崔大郎浇了一头冷水。
单单一个推广耕牛都这么难,应该说只要沾了钱的,百姓都以为是不安好心的贪官。
崔大郎叹气道,“不是说一头牛顶个两到三个劳动力吗,百姓要是买牛了,干活自然轻省很多。怎么只看到钱呢。”
章小水道,“四两银子,月息两分,三年的息钱就是两千八百八十文了。”
崔大郎没想到章小水算这么快。
上次他走了一个村子的私塾,大半学生都算不出来,另一半还得拨打算盘捣鼓半天给个错的。
章小水道,“近三千文的息钱,穷苦人家都可以添媳妇儿了。”
“而且,手里都没余钱余粮谁敢赊欠,那利滚利谁知道后三年老天爷赏不赏脸,是干旱还是水涝?不买牛,庄稼户就是辛苦点,但累的安心踏实,不会总想还有外债没还。”
尤其今年干旱,都做好勒着肚子活了,这时候谁会买牛。
崔大郎道,“那买牛解放了劳动力,老百姓的土地就可以精耕细作,这样地息好,不是正向的好盼头吗?”
章小水笑道,“以为老百姓是懒啊,一家虽然二三十亩地,全天都在地里忙活,起早贪黑的忙,可地瘦不出庄稼。”
在村子里想活命吃饱穿暖,基本没懒的。
沾了一个懒汉名头,可不得十里八村都出名,那更加说明稀有。
崔大郎疑惑,“那你们山狗村的庄稼怎么就比别的村子好?”
章小水道,“自然是沤肥了。肥料足。”
崔大郎道,“那别的村子难道不知道沤肥?”
章小水心想这是哪的富家公子,怎么完全不懂农事的样子。
就好像没在村里生活过。
章小水看着崔大郎一身破烂的粗麻陷于了疑惑,尤其是那肩膀上粗麻开了线头,露出了顺滑白亮的中衣一角。章小水和周小溪去布庄铺见过这种布料,是天价的绸缎。游商可没他这派头。
电光火石间,章小水隐约明白了他阿爹对这人的态度,以及想到这人一听他夸县令就欣喜的模样,心里一下子全明白了。
章小水霎时有点懵。
县令啊,就这样掉山坎河边里了?
还被他驮牛背上被村民拿锄头围观了?
就是他们村子来一个收税官都称呼大人的,里正都要对差役毕恭毕敬前呼后拥的。
章小水正游神震惊之际,就见对面坐的县令捧着他家的破土碗,十分享受的抿了一口茶水,眉目舒展很是惬意的模样。
哈哈,县令原来也是凡人哦。
章小水刚刚颤了颤的心脏,见崔大郎丝毫没架子的模样安稳很多。
他道,“其他村子也会沤肥啊,但他们只会丢一些草河泥和家肥埋在地里,或者在地里烧土肥。这沤肥的法子说着简单,可各种东西混合出的肥力不同,有的适合水田的,有的适合山地的,而且比例和发酵天数温度都不准确,那出的肥效就千差万别,就是最简单的烧土肥也是一样的道理。这还得看庄稼户的个人手感。再说,每个土壤要的肥都不同,好比沙地、黄土、黑土……”
章小水说的头头是道,崔大郎听了才发现种田原来还有这么些细节。
难怪前朝有人编撰了一本农书涉及沤肥的法子能得到天子青睐,直接连升两级。
崔大郎又有些奇怪,那山狗村会沤肥的人家是怎么学会沤肥的?且前朝也有推广沤肥法子,怎么华水县这边沤肥还是那么落后。
章小水道,“是我们村一个大婶她老家会种田,世代自己摸索出来的。至于前朝推广什么法子,我年岁小不知道。不过……”
章小水顿了顿,还是道,“也听说书的讲,有的官员不重视农事,不管百姓庄稼如何。四年一调任,在农事上投入的产出收效慢,不及其他商户收税显著。”
崔大郎看向李瑜,这说书的先生怕就是这位主人家夫郎吧。
倒是说的没错,即使朝廷有新的种子和沤肥法子推广,可地大物博地貌气候都不一样,真放地方上推行,不得反复实验个好几年。农事周期太长了,官员调走前都没个结果,对官员功绩并无益。
种种原因导致地方上农事落后,百姓基本上只畏惧衙门,没有打心底的敬。
崔大郎心里叹息,正想着胸中一展抱负时,就听章小水笑得特别开心的道,“不过我们这位新县令大人就不一样了,他又是耕牛又取消入城税的,一看就是心系百姓的好父母官。”
“而且现在县城里的风气治安都被新大人管好了,白天的商贩和晚上的夜市明显比以几年前热闹的多。”
“我家两亩田种姜,租一亩水田种稻谷,两亩旱地种杂粮,三亩麻地,家里三个劳动力,全靠这个也吃不饱饭。我家平时还会进山打猎,杀猪,但这样也只勉强维持温饱。种田靠天吃饭,就像今年老天爷不赏脸,万一年成不好闹饥荒,我家又没余粮全家都得饿死,所以我家就要想办法另谋出路了,想进城摆摊做点小吃。那这样人手就不够了,就要买牛来缓解下。”
崔大郎还想他们家要怎么谋出路,一听是进城摆摊,有些不看好。
农家子多数连大料都认不全,就是酱油和醋都很少有人买,给了好东西都不会做。这是他蹿乡走访得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