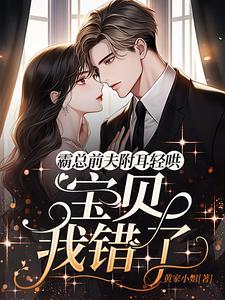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诗词 白云 > 第81章 觉山塔影映心痕(第1页)
第81章 觉山塔影映心痕(第1页)
云麓词心录:第八十一章觉山塔影映心痕
暮春的风裹着杏花的微香,从雁门关外蜿蜒而来,在煜明的青衫上染上一层浅淡的光阴。他站在长途客车的窗边,指尖摩挲着掌心的檀木佛珠,望着车窗外飞掠的黛色山峦,忽然想起三日前在云冈石窟见过的飞天壁画——那些衣袂翩跹的仙子,是否也曾俯瞰过这般连绵的青翠?
“煜明,下一站到灵丘县了。”同行的苏绾轻轻叩了叩他的肩,手中的笔记本还摊开在记录云冈题记的那页,墨色未干的小楷旁画着几簇莲花纹样。她是大学里研究古代建筑的学妹,总爱用写本捕捉每一处古迹的轮廓。
客车在山路上拐了个弯,远远望见觉山寺的砖塔如一支毛笔,斜斜插在苍青的峰峦之间。煜明忽然想起去年在敦煌见过的经卷,那些被时光侵蚀的字迹,竟与眼前塔身的斑驳有着相似的韵致——都是岁月亲手写下的诗。
一、塔影初逢:砖纹里的千年光阴
晨雾未散的觉山寺门前,两株古松如守门的老僧,枝干虬结间漏下细碎的阳光。煜明踩着青石板拾级而上,鞋底与苔痕相触的声响,惊起檐角一只灰雀,振翅时抖落几片陈年的瓦当残片。
“师兄你看,这塔基的莲花纹砖,和《营造法式》里记载的‘宝相莲’几乎一样。”苏绾蹲下身,指尖轻触砖面上浅浮雕的莲瓣,睫毛在眼下投出蝶翼般的阴影,“辽代匠人竟能把坚硬的青砖,雕出绢帛般的柔软感。”
煜明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砖面上的飞天正捧着莲灯翩然起舞,衣带在风中似乎还能飘动。他忽然想起在故宫见过的辽代木雕,那些被岁月磨去棱角的线条,却在沧桑中沉淀出更动人的温柔。掏出随身携带的宣纸,蘸着山泉水写下半阙《鹧鸪天》:
青砖雕就彩云衣,千年风露未曾曦。
飞天袖底莲灯暖,照破人间第几期?
墨迹未干,忽闻塔内传来轻轻的诵经声。循声而入,阴凉的塔内弥漫着若有若无的檀香,斑驳的壁画在昏暗中若隐若现。一位鬓角染霜的老者正持着放大镜,专注地观察着墙角的一处彩绘,镜片后的目光如古镜般清亮。
“老先生可是在研究这壁画的矿物颜料?”煜明想起在敦煌听研究员讲过,古代画师常用石青、石绿等矿物色,历经千年仍不褪色。
老者转身,眼中泛起微光:“年轻人竟懂得这些?这处‘药师经变图’的衣纹用了唐代‘铁线描’,但敷色却是辽代特有的叠染技法。你看这菩萨衣袂上的金粉,虽已剥落大半,却仍能想见当年‘金身映日’的盛景。”
他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夹着银杏叶书签的那页,上面画满了塔砖的纹样与笔记:“觉山寺塔重建于辽大安五年,八百年来历经七次地震,塔身倾斜却不倒,全凭这‘五十四券’的中空结构。这些砖雕看似装饰,实则暗藏力学玄机——你看这斗拱砖,每一块的弧度都经过,方能承托起十三层密檐的重量。”
煜明望着老者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砖纹上轻轻划过,忽然想起自己的祖父。老人临终前也是这样,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家中祖传的青铜器,说每一道纹饰都是祖先与时光的对话。此刻塔内的光线忽然明亮了些,壁画上的飞天仿佛转动了衣袂,将千年的光阴,都收进了老者眼底的温柔。
二、壁画寻幽:丹青里的往生世界
午后的阳光从塔窗斜斜射入,在壁画上投下菱形的光斑。苏绾支起画架,准备临摹那幅“维摩诘经变图”,笔尖在调色盘上踌躇许久:“师兄,你说古人画这些壁画时,是否真的相信画中世界可以往生?”
煜明望着维摩诘居士手中的羽扇,扇面上的山水竟与窗外的觉山有几分相似。想起在京都见过的平安时代绘卷,画师们总爱将现世的风景,融入佛国的幻境。“或许他们相信,每一笔勾勒都是在搭建一座桥梁,让尘世的灵魂,能顺着这些线条,抵达心中的净土。”
墙角处,一尊残损的胁侍菩萨像静立着,虽已失去头颅,衣褶却依然流畅如流水。煜明忽然注意到菩萨足下的莲台,竟与塔基的砖纹一模一样——原来地上的莲花,早已在千年之前,就托举起了云端的信仰。
老者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旁,手中捧着一本《觉山寺志》:“这塔内的壁画,曾在明代被重绘过一次,但底层的辽代画稿仍有留存。你看这处‘西方净土变’,水波纹里藏着的小沙弥,便是后世画工不经意间留下的‘时光印记’。”
书页翻动间,一片干枯的枫叶飘落,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四句诗:
塔影沉沉日影斜,丹青剥落见袈裟。
当年笔底生花处,犹有香风绕梵家。
“这是清代一位僧人留下的题壁诗。”老者笑道,“百年前他在塔内修行,每日对着壁画参悟,最终在枫叶上留下这几句。如今枫叶已枯,诗却还在,就像这壁画,颜色会淡,故事却永远活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煜明忽然想起去年在江南见过的古桥,石栏上的对联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却仍有行人驻足辨认。原来真正的永恒,从来不是物质的不朽,而是那些被代代相传的凝视与叹息。他摸出随身携带的狼毫笔,在老者的笔记本空白处补全了那阙《鹧鸪天》:
风过回廊惊宿鸟,雨侵砖缝长新荑。
摩挲旧迹浑如醉,忽听山僧说劫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