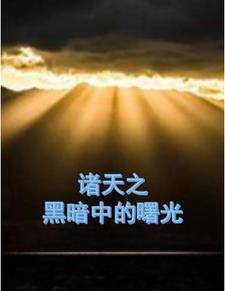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同居后标记了omega情敌 > 第52章(第3页)
第52章(第3页)
“可是你也真的很像嘛!”余晓晓理直气壮,伸手去戳她因为嚼着食物而微微鼓起的脸颊,“你看,大冰块,一模一样——”
随后,她又捏了那个小小的、可怜的大福几下,才把它吞进了肚子里。
“……你也很像。”
“像什么?”
“小河豚。”向舒怀就说,认认真真在说,神色里没有一丝促狭的痕迹,“刚刚在厅里的时候,你气鼓鼓的,特别像。”
余晓晓噎了一下,突然想起来自己刚刚的郁闷。
“还说呢,大冰块!”这么一想起来,她便理直气壮地瞪圆了眼睛。
“还不是因为你和那些人一直聊啊聊,不知道怎么那么开心,根本一点都没注意到我在旁边……大冰块,从实招来,你刚刚和那个小姑娘说什么了?”
向舒怀有些困惑地皱了皱眉毛:“……谁?”
……就是说,大冰块对那个女孩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喽?
余晓晓暗暗开心了片刻,试着形容:“就是那个,浅棕色卷发的小姑娘,比你矮不少,很小一只。”
“啊,她啊。”向舒怀点点头,“我们说了……嗯。”
她这么说着,不知是想起了什么,神情里忽然浮起些许柔和的笑意来,“……秘密。”
——???!!
余晓晓一下子瞪圆了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她神情轻松的面容。
“……大冰块!!”她抬高了声音控诉,“呜哇,你还说你不是来相亲的!你看看你的表情——”
向舒怀神神秘秘地望了她一眼,摇摇头,自己不说话了。
“大冰块,大冰块,”余晓晓一下子缠上去,倒在她旁边,“到底是什么嘛,不要这么神神秘秘的嘛,你们到底说了什么我不能知道的——”
见向舒怀仍然不肯回话,她干脆去碰对方软乎乎的腰部,誓要让这个可恶的大冰块求饶。
“……啊呀、余晓晓!”
被碰到痒痒肉让向舒怀一下子笑起来,用力挣扎起来,偏偏推不开余晓晓的手,本身又处在下位。
她被压在柔软的沙发上,挣又挣不脱,被弄得连连求饶、边喘气边笑,眼眶都要红了:“余晓晓,啊、我错了,余晓晓……”
余晓晓就不依不饶地继续逼问:“快说,向舒怀,快说你们到底说了什么——”
最终两个人都闹得累了,余晓晓一下子在她身边躺倒下来,肩挨着肩、一起喘着气,不再动了。
她微微侧过头去,只看见在沙发的凹陷里,两人的长发仿佛织在一起般,深黑的柔软直长发属于向舒怀,而更浅些、微微翘着卷的硬发属于她,映照在逐渐落下的夕阳里,如同两条交汇的、粼粼的涓涓河流。
在河流一畔,她看到向舒怀因为打闹而泛着微红的脸颊,那双黑眼睛剔透而明亮,泛着鲜活而生动的神采。
……余晓晓不觉伸出手,轻轻地触碰了对方柔软的面颊。
向舒怀于是转过脸来,也安静地望着她。
——而余晓晓的手指在两人发上流连许久,仔细地、慢慢地梳理着。
然后,她将两人的头发轻轻缠绕在一起,编成一个松松的结。
向舒怀只是注视着她的手指,认真而出神。
她们谁也没有讲话。
空阔的、饰满了秋日鲜花的露台里,在高大绿植的遮掩后,她们仿佛与玻璃里头繁华的觥光鬓影彻底地隔绝开来,只是处在另一个与暗色天空交界的安静的小世界。
只有她们两个,肩挨着肩、头靠着头,时间仿佛也为她们而停止了无情的流逝。夕阳不再下落、美酒不再从瓶口跌入杯中、细细的花蕊不再因为微风的吹拂而轻颤。她们没有牵手,长发却交织成同一道静谧地流溢的河流。
大概是工作还是太累了,向舒怀倚着她的肩膀,已经困倦地阖上了眼睛。
“你要在这里打个盹吗?”余晓晓小声说,怕惊走她的那丝困意,试着握握向舒怀的手,“好像有点凉……”
而向舒怀只是小小点了点头。
——余晓晓于是褪下自己的西装外套,往向舒怀的方向靠了靠,将外套给两个人盖上。
然后,她也闭上眼睛。
在身侧彼此的温度里,她们静静地靠在一起,早已逃离了宴会的繁华与喧嚣,彼此陪伴着沉入了安宁的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