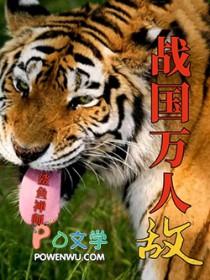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捡来的皇子夫君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梁元帝一面说着,手上一面投食,喂给敞厅清池里好生养着的龙睛鱼。
云岩斋多用于君臣议政,他们父子俩独自来到此处议事的次数也不算少。
梁元帝停下喂食,伸手接过内监李进忠递来的冰碗,用羹匙舀起炎夏中冰镇过的妃子笑,放入口中。
沈行密揣摩着梁元帝的话中之意,谨慎接道:“其中症结,在于义仓中的谷米虽是取之于民,却并未给予相应的报酬。因而出售陈谷所得的钱款,理应用作购进新谷的银钱。但理是这个理,实际的情况却是时下的官员往往会将这笔售卖陈谷的银子挪作他用。”
“如此一来,仓中谷米就难以及时补充,义仓谷米短缺,在天灾到来时,外城仓米尽数散出以后灾区很快会再度遭遇饥荒,重陷窘境。”
梁元帝听罢,没有说他答得对还是不对,只说了句:“你认为,你皇姐这次能办好么?”
沈行密对自己这位父皇还是有些了解的,他既不予置评,就表明认同了他的说法。
但听他提及沈缇意,沈行密心中骤然不可遏制地升起一股怒意,昨日府上的人将魏礼群的来信送到他手上前,他还满以为自己万无一失,魏礼群经自己的授意必定令她进退两难,只要到头来功亏一篑,她便会失去父皇宠爱,就像她娘一样,当一个人人可欺的窝囊废。
结果他越读那信,越是火冒三丈,最终将那信撕得粉碎。
沈缇意,即使她身上挂了巡抚名号,是怎么敢随意处决朝廷命官的?
沈行密气得狠了,本想抓着这一点参她一本,谁料她手里不仅捏着证人证物,还搬出了“事急从权”这座大山,只要官绅缴纳赎金,不动私刑也不谋私利,挑不出什么大错。
当下连梁元帝也特意问起她的状况,自己贸然上折,怕是讨不了好,届时再给梁元帝留下个争权夺嫡的恶劣印象,更是有损他在外苦心经营的名声,到时适得其反,便只好作罢。
沈行密压下恼意,不显山不露水地答道:“二姐才德兼备,定不负父皇所望。”
话毕,梁元帝笑起来,没有再谈及沈缇意,他又咽下一枚蜜荔果,后朝沈行密递过冰碗:“闽都送来的妃子笑,尝尝。”
沈行密接过来,手心被碗壁染得沁凉,又不能撒手。
他囫囵咽下果块,唇舌都发凉,忽地觉得身上有些冷,轻轻打了个哆嗦。
酷暑之下,云岩斋设了数十架金盆,御驾亲临时便将事先冰镇在盆内的新鲜瓜果和饮品取出食用,消热祛暑。
金盆内部的冰化开时会吸入四方的热气,又从盆顶的镂雕小孔放出凉气,整个云岩斋可谓不知人间有尘暑[壹]。
此时正是三伏天,沈行密来觐见梁元帝已经有一会儿,刚来时觉得热气腾腾,现在却感觉周身都在战栗,几乎要呆不下去。
梁元帝看他的肩膀在小幅地发抖,待问清楚情由,又吩咐李进忠拿来备好的衣物给沈行密披上,失笑道:“行密,你这身子骨怎么比当值不惑之年的朕还弱呢。”
“你是大梁未来的储君,身子要小心顾着。”
沈行密连忙称是,大梁的太子一直未定人选,他自然也在储君之列,但经由梁元帝亲口说出,还是难免让他心旌摇曳。
在外人看来,他是梁元帝沈璩最喜爱的儿子,母妃亦是宠冠后宫,梁元帝的心思谁也猜不准,若真的喜爱他,就应当立他为太子才是。
但梁元帝没有。
他的心思好像放在每一个皇子身上,没有表现出任何实质的偏袒,仿佛放任了他们几个兄弟明争暗斗。
邵州,知州府。
卫辽吩咐了家仆用提篮装上瓜果,而后将提篮绑于辘轳之上,送下水井,令瓜果浸于清凉的井水中。
“公主,这便是‘六月都城偏昼永,辘轳声动浮瓜井’中的‘浮瓜沉李[贰]’了,小地方招待不周,这些瓜果给公主解暑。”卫辽解释道。
夏日炎炎,邵州不像皇都架上金盆,但他们自有一套取用冷食的做法。
沈缇意打上京来,卫辽怎敢怠慢。
“有劳卫大人。”沈缇意打仗时什么苦都吃过,并不如安居在上京的皇亲贵族娇生惯养,何况灾情肆虐,她知道卫辽不容易,也不会故意挑刺。
她吃下几块切好的果肉,正好碰见祝续玖回来。
两人的视线隔着点距离交汇,好几日不见,祝续玖倒也没怎么变,哪怕裹着一层热气,还是如初见一般风度翩翩,行走间那股子从容的气度,就算相较显贵人家的公子,也是不落下风的。
沈缇意看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老的僧人和几个小和尚,便明白祝续玖这一趟没白走。
她在祝续玖还没开口之前就将果盘递给他,一抬下巴:“做的不错,今日先休整。”
“谢公主。”祝续玖双手接过盘子,脸上又出现那种温良的笑容,很讨人喜欢。
他睁着那双大而圆的眼睛,很像沈缇意小时候养过的一只圆滚滚的松狮犬,让她有点想摸一把他的脑袋。
实话说,是初次见面时便想了,但她按住了自己的手。
不是不想摸,而是他是自己新收的人,她一摸完是让自己爽快了,却会让他失了威信,今后还如何在外人面前立威。
“方丈远道而来,缇意十分感激。”沈缇意目光转向后方的僧人,两手合一,微低下头,她虽贵为一国公主,对外人也十分讲究礼数。
“佛家讲究普度众生,出家人当慈悲为怀,公主此番也是顺应时局,实乃明智之举。”住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