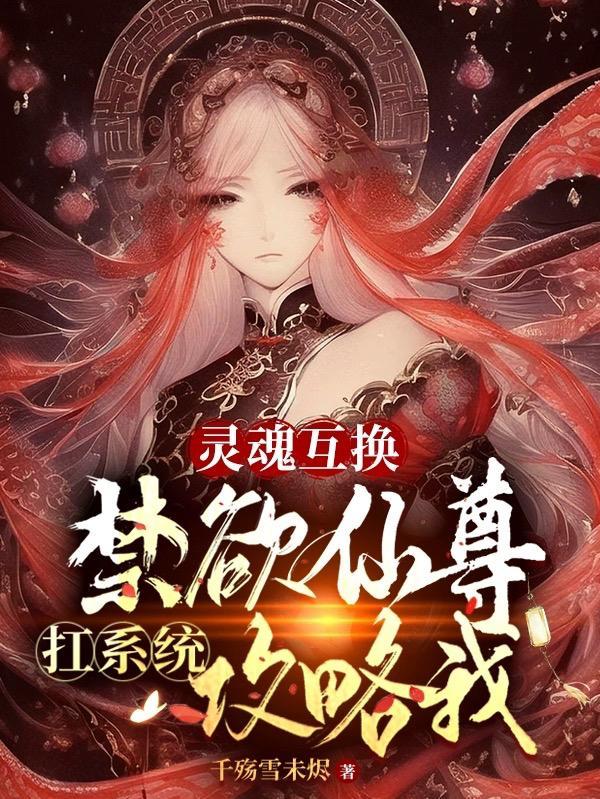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综影视现 > 第19章 西游记-历劫骊歌行世界17(第1页)
第19章 西游记-历劫骊歌行世界17(第1页)
瓷瓷一向不太关注朝事,只轲偶尔会挑着跟她絮叨一些。
但最近几日,轲似乎都有些缄默,不太得劲的样子。
瓷瓷便问了缘由,轲告诉她说:“太子要被废了。”
不是惊马重伤刚病愈吗?
帝后也多有宠爱,为何有要被废了的话?
轲解释道:“太子多有狂悖,此前被陛下训斥多次了。这一次伤了腿,我给他送了你做的药膏,但他不信我,并没有使用,落下了残疾。失意之下,一连做出几番失智若颠的举动。父皇,已经在暗示大臣提议重选太子了。”
“他没用药膏?”瓷瓷心想,那药膏有续筋接骨之能,太子不知珍惜机会,果真如她早前所想,皇室贵胄都是她很难理解的存在。
“当时,”轲闭了闭眼睛,“当时太子以为我是去笑话他的,把药膏直接砸了,”说到这里又紧握了一下瓷瓷的手,“而我当时没有多劝他。”
瓷瓷明白他情绪为什么不对了,“自来太子之位就不好做,能善终顺利即位的太子寥寥,他这样退了,未必不是好事。”
轲看着瓷瓷的关心,知道她是懂自己的,笑了笑说:“我知,太子的腿,不知道以后可还有机会治好?”
瓷瓷听明白他所说的以后,是指下一个太子坐稳位置以后,她点头说:“可以,那个药膏不多,但效果很好。”
轲便没有更多的问题了,他和太子是兄弟,更是敌人,能替太子想到这个程度就足够。
“你说想与我回周州白,”轲摸了摸瓷瓷顺滑的乌,“我得推一个不会妨碍到我们的新太子上去。”
正是这个话!
若是上位者敌视,岂不是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所以在回周州之前,推选一个合适的太子是很必要的。
轲笑着说:“就是能陪你的时间少了,你若是无聊,就去找歆楠玩,你们姑嫂二人带上侍卫出宫去也行。”
“来日方长,”瓷瓷亲了亲轲,“回了周州,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你说得对。”轲抱起瓷瓷,任由自己的后背砸上软榻,扣着瓷瓷的腰和头,深深浅浅地吻着。
瓷瓷觉得自己应该是不重的,不然她压着轲这么久,轲怎么还有那么深的气息?
想到他们的大婚之日也没几天了,瓷瓷走了神,惹得轲不满,“居然不专心——”说着微微用力地咬了她一口,瓷瓷不愿意吃亏,两人角力一般翻滚起来,轲又怕软榻窄小,瓷瓷万一翻落磕到,遂在她躺到一个合适位置的时候,紧紧压住,整张脸埋在她微敞的锁骨处,声音低低地求饶,“我错了,我认输,饶了我吧。”
瓷瓷不再动,轲便开始仔细地寸量她今日穿的素纱低胸襦裙。
“口水——”瓷瓷不耐地推着他的脑袋,比较敏感的地方,太过轻浅的触碰反而难受。
“乖,”轲自己把口水又吮吸回去,变为微微用力的啃咬。
瓷瓷冰肌玉骨,很少穿这样展露身材的裙子,他不敢掀开裙边,但能够触及的柔软已经让他脑袋晕乎,颤颤巍巍了。
瓷瓷感受到了变化,也曲膝动了动,直到这条裙子又被轲丢进火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