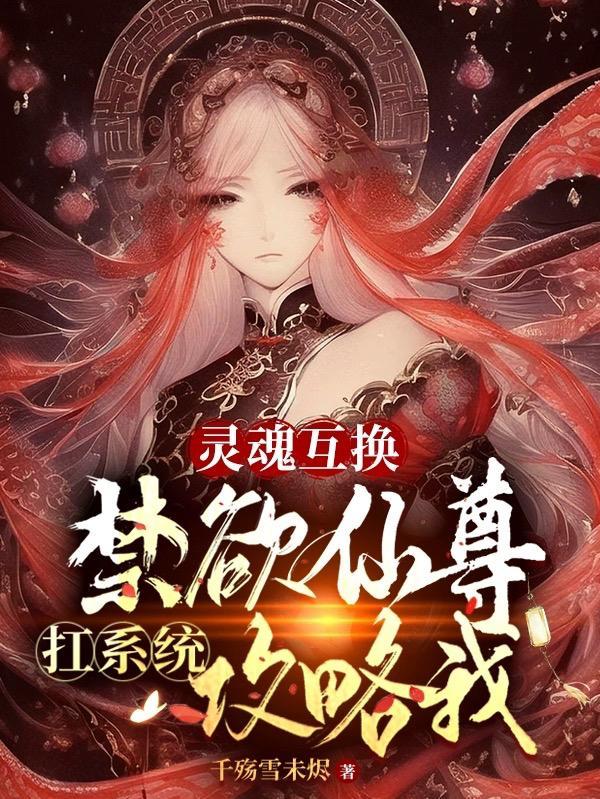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嫁给男神后被宠上天 > 第24节(第2页)
第24节(第2页)
也不知道是因为白天用脑过度太辛苦,还是这药的作用真这么厉害。连续半个月,沈似故沾床就睡。
疏恙最近做节目偶尔回家住,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呼呼大睡。
晚上疏恙录完歌回来也不过才九点半,洗澡吹头发动静那么大也没能吵醒沈似故。
他在床边坐了会儿,俯身亲了一下她的脸,“阿故?”
沈似故一点转醒的迹象都没。睫毛都没动一下,安静恬静,一如当年那甜美率真少女。
疏恙去书房收了十来封邮件,给国外的合作商聊到十一点才回卧室。
睡觉从来不会老实的沈似故连睡姿都没换。
疏恙侧躺着,将她捞进臂弯。
窗外有稀薄的月光洒进来,花园里树枝摇曳,她身上穿着新买的睡裙,小腿露在被子外面,白的反光。
他垂下眼,盯着她的嘴唇看了几秒,忍住不低头吻她。
沈似故感受到肺部的压迫感,愣怔地张开嘴大口呼吸,四肢和心脏无法同时给出脑子反应,她呆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过什么。
疏恙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带着压抑与沙哑:“醒了?”
他这么弄,还不醒,那她得是睡得多死。
沈似故惊喜地发现,这一次全程都没有痛楚。快乐得像朵软绵的蒲公英,轻轻摇晃,再缓缓下降,慢慢地落入他掌中。
她身体崩得很紧。尽兴而归,眼角湿润。
在这段婚姻里,她从未尽兴。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快乐。她只在乎他的感受,活得像个木偶。
最可怕的是,能意识到这些,却又甘愿当个木偶。
她在心里问,沈似故,你在吗?
见她掉眼泪,疏恙将她的脑袋按进怀抱。
怕她发烧,他只能克制。之前总认为是她不听话要撩拨他,今晚她明明睡得很沉。
都是借口罢了。
疏恙试图帮她缓解,“还疼不疼?”
沈似故边哭边摇头,摇头又点头。
他不知道她对他的手也有执念,想帮她减轻痛楚。
沈似故背过身去避开,用仅存的一丝力气阻止。
她气若游丝:“别碰我。”
疏恙心底的那点愧疚荡然无存。眼中的温情被冷漠替代,他把她禁锢在臂弯,肆意掠夺。
沈似故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老公?”
“嗯。”
他突然变得很冷淡,沈似故委屈的不行,明明是他把她弄醒的,还凶。
往他怀里钻了钻,枕着他的胳膊,刚闭眼睛,又被他叫醒:“阿故,你看清楚,我是谁?”
沈似故一丝力气都没了,动了动眼皮,侧目看他:“啊?”
疏恙一字一顿,语调没有一丝温度:“我是你的合法丈夫。”
能不能不要再惦记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