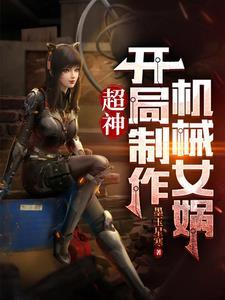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家父宋仁宗作者御风流 > 第八十三章 庆历五年上(第2页)
第八十三章 庆历五年上(第2页)
“李叔李叔,对不住,这小子嘴上也没个把门的。”
“没事,年轻后生嘛,都有这一遭。”李叔还是笑眯眯的,但手中的报纸已经放到了桌上。
飞踹一脚之人赶忙将手伸入怀中,摸出两颗银粒子放在桌上,面色隐带讨好:“李叔,这街坊邻居的……”
“你啊……老了老了,赶不上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时运了。”
李叔点点他,然后用手盖住了两粒银子,然后快速低声说道:“报上没说。但都说这报纸是东宫的产业,近来又风传官家有意把报社入官。”
华夏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最讲究的就是一个言尽而意无穷。
掏银子的汉子琢磨好半晌才明白过来,东宫又和垂拱殿斗法呢。
辽夏两国的使臣能不能来,来了能不能按时到,还得看东宫的意思。
不然两国使臣入边境军州后能有一百种理由迟到。到时候官家不下诏怪罪就不错了,赏赐更是想都不要想。
不过东宫打去年大胜武进士之后偃旗息鼓快有半年,怎么又折腾上了?
莫非是静极思动?
他规规矩矩道了谢,又像拎小鸡仔似的把刚刚那个出言不逊的弟兄给拎走了。
等过了两条街,茶摊的幌子彻底看不见之后,有人问道:“四哥,作甚如此尊崇那老头,偌大的东京城里,又不止他一人识字。”
看来团队中对要价比旁人高出三成的李叔不满者众多。只是有老大在上头压着,这才面上一片融融之态。
“放你的罗圈屁!不会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四哥横眉立目的龇牙模样把所有人都吓得噤若寒蝉。
“还识字的人多呢,咱们今后,不说今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日子都得指着李叔了,千万不可得罪了他。”
“四哥,这又是为什么?”有人壮着胆子问。
“唉,我真是。你们两个眼睛都是长来透气的吗?没见到打开年起范相公就上箚子说兴学校、修水利、筑道路吗?到现在又加了办报社。
“咱东京报社十四士里头除了早年间三位因张扬受贿被闲置黜落的,还有两位大总编动不了,其余的都跟着去了地方兴学校报社。又说这些学校都是仿讲武军校之例,入学全免,优者还有钱粮补助。
“你们就看看东京报社中那些编辑年初恩科中率,听听报社欲要入官的消息。
“除了李叔这样早已熄了科举之心的,哪个读书人能不心动,定会削尖了头往里挤。与前程相比,咱们给的那点散碎银钱算什么。怕咱们坏了名声,躲还来不及呢。”
有人持反对意见:“可是四哥,我听说那些从报社考出来的举子授官地方都是偏州远县,穷乡僻壤啊,这还是什么好事不成?”
四哥揽住了发问之人的肩膀,反手指着自己的鼻尖:“知道为什么你们都认我做大哥吗?”
一干人齐齐摇头。
“因为你们不动脑子。瓦子里的说书先生都说了这官场上要想升官快,最重要的就是要朝中有人。
“杜相的女婿,故王丞相的那个外孙子,苏舜钦,被御史中丞王拱辰盯上,参了一本挪用卖公文废纸的钱吃喝召妓。
“若非太子殿下训斥后力保,整个进奏院怕是得有半数的人被带累着削职为民。
“结果你们也看到了,此次兴学校,他的名字在众人中排第一。
“虽说去的是崖州,但蒙驹一个无官无职的夷人都因为在环州将报社办得红火得了嘉奖,眼看就要授官加职,他还能差了?”
“四哥,这是不是就是话本子里说的花金子买马骨啊?”
“还是你小子机灵,但你记好了那叫千金买马骨,拽文哪能只拽半截的。”
“哈哈哈哈哈。”其他人都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声。
“好了好了,都别笑了。咱东京城里肯定是也要办学校的。
“南城的郑六和我相熟,他提前收到了风,说是这回不仅要办考文武进士的学校,而是,而是要整什么百工之学,有种庄稼、敲算盘、背药箱的。”
“四哥,这敲算盘和背药箱的咱们暂且不去说它,只这种庄稼,谁还不会啊。”
“就是就是。”
一直和兄弟们笑嘻嘻磨牙的四哥第一次怒了,毫不客气地给了每人一巴掌。
“要你们平时多听多看多想,都不听。前些时日民生报上才写了,这庄稼和庄稼之间是不一样的。
“正因先帝朝时有夷人献了好的稻种,现在江南一带才能有余粮往咱东京城运,咱们这些不种庄稼的才能饿不着肚子。”
有人抓挠着被打疼的地方,借着外力开始思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好的稻种也能产更多的稻子?”
“就是这个理。我可提醒你们一句,报社刚建的时候,没人想到他们能入官,随便一个进士都能往里伸脚。
“现在咱们殿下又修了一座农庄,据说在里头捣鼓种庄稼的事,又要开种庄稼的学校……”
这些人只是还没寻到适合自身上升的途径,而不是真的傻。
几年下来,东京城的百姓都明白了一个朴素但有效的道理:“跟着太子殿下走,准没错。”
想通此结,顿时就有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起来。
这学文练武的有报社和讲武军校在前,肯定有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挤,他们肯定没戏。
但这种庄稼敲算盘,那些少爷羔子肯定比不过他们。而且即便将来得不到官做,那也是一门手艺,缺不了吃喝。
四哥见状提醒了一句:“据说只要八岁到十五岁的孩童,各科略有不同,咱们是没机会了,你们家中有适龄亲戚的可以先透点风,说不定咱们以后也能有做官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