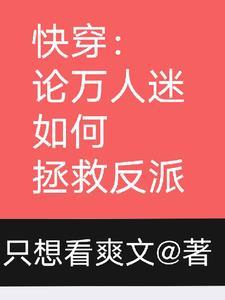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公公被按在酒缸里结果儿媳妇出手相救是什么电视剧 > 第47章(第4页)
第47章(第4页)
不过她不得不承认,这位谢先生身形颀长,面目俊雅儒秀,这沉稳大气的颜锦衬得他如美玉明月,既好看又不失温润含蓄。
谢景修却在烦恼别的事,颜凝在这个地方,身为女子却要宰杀牲口。
且不说杀生不祥,单论这活计的肮脏可怖,就不能让他的阿撵做,碰一下都不应该。
又嫌弃又心疼。
他叹了口气坐在一棵树桩上,文雅气派的举止与残糙的树桩格格不入。
“你想问我什么?”
眼前的人神色温柔,目光沉沉注视自己,颜凝突然忘了自己想问的事,小脸一红,有点尴尬。
“嗯……我想问什么来着?啊是了,谢先生从关内来时,有没有遇上或是听说哪户人家不见了女儿,亦或谁家名字里带“凝”或者“雁”的?”
谢景修心头一跳,不动声色看着颜凝问她:“你很想找回你的亲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名字里带了这两个字?”
颜凝略带忧伤地笑了笑,“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不是我有多想,只是万一有家人在担心我,而我行踪不明,或许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也不来找我,只顾着自己伤心,那就太可怜啦。”
说到这她从脖子里扯出一根红绳,下边坠了个透明小物,踟蹰了一下后取下绳子,把印章递给谢景修看。
“我身上有个琥珀印章,上面刻了“凝鸣雁舒”四个字,《凝鸣》诗经里有,宋祁则写过一《舒雁》,但合在一起我就不明白了。
或许是我父母或是家人的名字,也可能是他们送给我的,刻了我的名字。”
谢景修接过印章,热乎乎的还带着颜凝的体温,他记得这个小东西应该是正好坠在她双乳之间的,胸腹忽而一阵躁动,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
这是他亲手刻的印章,她却说什么“父母送的”,实在令人心冷,谢景修看着印章上的字微微一笑。
“说实话,我不觉得这是父母会送的东西,你挂在颈间贴身携带,倒像是情郎送的。
说不定“凝”“雁”两字是从你们二人名中各取一字。
若真是如此,你的情郎还在痴痴等你回去,你却要在这里结婚生子,唉……可怜啊。”
“额……”
颜凝莫名其妙就被扣了个薄情的帽子,心里老大不舒服,但又觉得谢景修的话很有道理。
自己这年纪,有个喜欢的人也不奇怪,这东西万一是定情信物呢?
这人不送饰珠宝,送个印章,想来也是个有雅趣的读书人。
谢景修看小颜凝盯着印章若有所思,又添油加醋地说:“你看,这琥珀里有一只红色的小蚂蚁,这叫红豆蚁,意表相思,十有八九是你的心上人给你的。
我看你还是不要和那几个男人纠缠不清了,不然哪天脑袋好了,突然想起了以前心爱的人,还不知怎么后悔呢。”
什么叫“脑袋好了”,我脑袋哪里不好了,受伤失忆而已,为什么要把人说得像犯病的笨蛋一样。
颜凝撇撇嘴看了谢景修一眼,从他掌心拿回印章戴上,不高兴地说:“我没有和人纠缠不清好吧。”
“没有那就最好了。”谢景修莞尔一笑,捣蛋鬼这气呼呼的脸蛋最可爱不过,让人想捏。
“如果让你在“凝”和“雁”两个字里挑一个做自己的名字,你想要哪个?”
“当然是“凝”啦。”颜凝毫不犹豫地嫣然回答,“凝多仙气,那可是神仙养在昆仑蓬莱的瑞禽。大雁土了吧唧的,因为不会叫被人射下烹煮了呢。”(典故出自庄周悲杀雁,本为不能鸣。)
“额……”
谢景修被她气得胸中气血翻涌,怒极反笑,眯起眼睛看着她点头道:“你说得不错,很有道理!”
颜凝莫名感觉背心升起凉意,头皮麻,身上结起成片的鸡皮疙瘩,不敢再看谢景修,也不明白哪里得罪了他,只好移开视线讪讪地说:“羊肉要烤好了,谢先生去吃晚饭吧。”
一只羊已经烤得差不多了,白天那个要射太阳的小伙子给颜凝切了一盘子羊腿肉端给她,油光闪闪香气四溢。
“谢谢。”颜凝接过盘子对阿木尔甜甜一笑,阿木尔红着脸喜滋滋地走了,谢景修看得火大,脸色就不怎么好。
“谢先生也尝尝吧,是为了您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才烤的羊呢。”
颜凝把盘子递给谢景修,他想起刚才血淋淋的场面毫无胃口,皱眉推拒道:“我不爱吃羊肉,而且没有筷子没法吃。”
其实颜凝也谈不上爱吃羊肉,但现杀现烤的确实吃起来香,这位矫情的客人连尝一口都不肯,未免太可惜了。
“那怎么办,总不能饿肚子吧。筷子我们有,您先坐着,我去给您拿一双过来。”
小颜凝温软大度,对上谢阁老这么难伺候又不给面子的人也不生气,她刚起身想走,就被谢景修隔着衣袖握住手腕。
“我的随从会拿给我的,倒是你,没筷子你准备用手抓吗?”
“大家都用手抓啊,啃羊腿怎么用筷子呀。”颜凝低头看了看被抓住的手腕重新坐回谢景修身旁,对他的疑问不以为然。
“你在关外待得久了,连饮食礼仪都不要了。”谢景修很是不悦,轻轻叹了口气。
这话听着古怪,好像他很熟悉自己一样,颜凝心中又生出白天初见他们一行人时的异样感,他真的不认识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