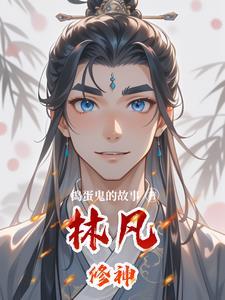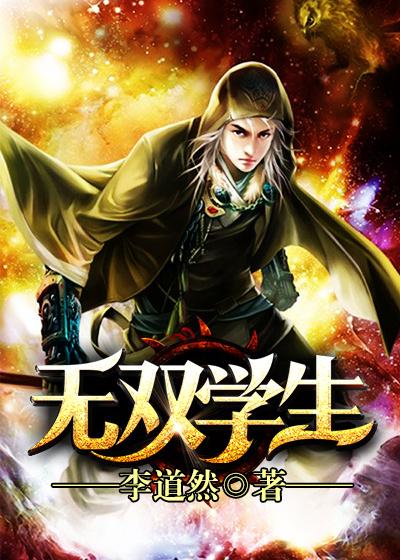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农家幼崽竹马日常免费阅读 > 第95章 农事官(第1页)
第95章 农事官(第1页)
章家姜病死了的事情,很快周围村子都知道了。
小井村的张木匠家这会儿正围着好些人,张木匠家今天从山里买了几根木头,需要人手帮忙。孩子大了,不论是分家成家都要扩建屋子。
一颗树男人腰杆粗,三百文一颗的松木,五百文一颗的枞树等等,一颗树砍回来就得四个劳动力扛下山。
这会儿院子的大木桩子上坐了好些麻布短打的汉子,说着闲话。
张春妮儿给他们端茶倒水的,都夸老木匠有个好孙女,老木匠笑呵呵的应下,是长大懂事了,以前冷倔的脾气横斜着脸好像谁欠她似的。这些日子突然就懂事了,洗衣做饭全村妇人都夸他有个孝顺的好孙女。老木匠心里别提多乐呵了。
就是有一点不好,还是不怎和他说话,背地里却经常给其他婶子婆婆说他的好和辛苦。
这孙女就是嘴巴太笨了。
张木匠又想难道是他平时不爱笑,太过威严了?
他家老婆子也说过他,每次当着外人乐呵呵的,回到家里就垮起个驴脸,像棺材板板。
这会儿一个汉子道,“诶,你们听说了吗,章家那姜坏了一亩地,挖了全烧了。”
张大郎一听就咂舌道,“咋就坏了?还烧了?”
“看来章家真的是财大气粗,看不上这点姜生意了。”
“屁,就是没成算,傻子。谁家会这样干,简直气的老祖宗都要骂醒。”
一群人都这样点头,面色肉疼的厉害,恨不得自己就在现场,不说阻拦,那好歹也能抢回来一点卖好几百文钱呐。
尤其这会儿地里的野菜都能卖个一两文,还抢手的很,那姜更不用说了。
眼见到了秋收,地里的庄稼没指望了,多空壳干瘪,秋收都没盼头了,谁家不是紧巴巴过日子。
“我之前就看到山狗村那河边冒着浓烟大火,没成想是在烧姜啊。那章家太老实胆小了,那姜坏了便宜卖撒,什么货色什么价格,又没骗人,烧了多可惜。”
在村子里,一般人家种的果子也舍不得吃,都是过年留着卖的。就好比那橘子柚子,怎么可能都是完好无损的,那磕碰坏的发半边霉点的,就贱价卖,好的五文一个坏的就一两文,还受人抢着买嘞。
水果贵,坏的还更好卖,同理,村民想姜也是这样。
不管咋说,都觉得章家太老实胆子小了,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发大财。
张木匠倒是觉得章家人品可靠,他当手艺人最重要的就是踏实,一个唾沫一个钉的。可惜他两个儿子离他身边久了,性子歪了,还瞧不上他这些东西,觉得他是个老顽固。
越想越觉得和章家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了。
张春妮儿听这些,也觉得可惜的很。
她还想听听情况呢,就听村里人话头说到了周家。
“周家那小哥儿绣手绢巾帕赚了钱,一条七八文,好的料子和绣品卖十几文的都有。”
“啊,这么赚钱的?比地里刨活还多。”
“这事情周围村子都知道,询问周家亲事的媒婆都多了起来。”
这下子家里有小子没订亲的都心思活络了起来。
可周小溪本意不是这些,他就是让那大黄村的人瞧瞧,他师父教出的可不是孬种,幸好没去一天十文的绣坊。拒绝他是绣坊的损失!
他现在绞普通的素面棉手绢,只裁缝收边一天能做十条,铺子里收五文一条。
但他加了点蜻蜓刺绣,也不麻烦,走平针混着打籽绣,但架不住他手巧刺绣灵动,一条就上到了七文。
一天可以赚毛利七八十文。这可是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快抵上周圆以前穿乡卖豆腐的了。别提周小溪现在正还是不知道累的年纪,觉得刺绣手工活儿,动动手指就好了。
他做多少铺子收多少,还是铺子守着他来。
之前章家姜地出事,周小溪帮忙扯,没心思搞活停工几天,那铺子派伙计守着送豆腐的周圆问情况。
得知只是休息几天,才松了口气,周小哥儿的帕子卖的格外好,就是十文一条也销货快。
“你说周小溪都会这么赚钱,那李瑜不是赚的更多?”
“这就不知道了,没听说过。”
“闷声发财呗。”
“我婆娘都心动想送闺女去学。”
“学那有什么好,要学费不说还得年节给人送礼,好不容易学会了出师了,那就要嫁人给别人家赚钱了。”
“那是的,吃饱了撑着想这些。地里收成不行,还是想想怎么过这个年吧。”
但还是有人好奇的,“那之前周小溪没选上绣坊,还以为他跟着李瑜瞎学,没想到李瑜是真有两把刷子。”
张春妮儿知道,李瑜一条缎面苏绣,那游鱼水草鲜活放阳光下都怕游出来。
周小溪说针法和绣法复杂,一条要刺绣半月,可价格也贵,三百文到一两都有的,还接客人的花样定制,布料客人也自己出,价格便更贵了。
李瑜自己一个月就能赚近一两银子,铺子老板劝李瑜勤快点,一个月多刺绣几条,可这东西费神费眼费心血,章有银父子三人都盯着,不让李瑜多做。
张春妮儿听周小溪这样说,心想李瑜怕是附近村子最有钱的夫郎了。
同村也有去镇上绣坊做工的,但都是已婚的绣工熟手,她绣工就顶多会打个补丁,她想去章家学刺绣。
现在还没分家,要去学了少了个人手干活儿,大房不乐意,事情就僵住了。
张木匠原本还不太想把孙女送去章家学刺绣,送一个,其他那些孩子怎么扯的清,要都去学,哪来的钱哪来的人去干活了。一家铁定乱糟糟的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