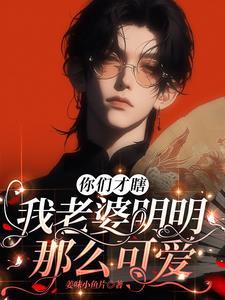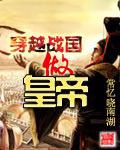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佛学研究十八篇评价 > 翻译文学与佛典(第2页)
翻译文学与佛典(第2页)
(8)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以晋隆安三年(西纪三九九)游印度求经典,义熙十二年归。凡在印十五年,所历三十余国,著有《佛国记》,今存藏中,治印度学者,视为最古之宝典(欧人有译本及注释)。在印土得《摩诃僧祗律》、《杂阿含》、《方等泥洹》诸梵本,《僧祗律》由觉贤译出,《杂阿含》由求那跋陀罗译出,显自译《方等泥洹》。自显之归,西行求法之风大开,其著者有法勇(即昙无竭)、智严、宝云、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僧绍(此七人皆与法显同行者)、智猛、道普、道泰、惠生、智周等,中印交通,斯为极盛。
(9)昙无谶中天竺人,北凉沮渠蒙逊时,至姑臧。以玄始中译《大般涅槃经》,《涅槃》输入始此。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金光明》等经,复六十余万言。
(10)真谛梵名拘那罗陀,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到中国,陈文帝天嘉、光大间译出《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大乘起信论》旧题真谛译,近来学界发生疑问,拙著《中国佛教史》别有考证)。无著、世亲派之大乘教义传入中国,自谛始也。
与真谛相先后者,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昙摩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皆在北朝盛弘经论,而般若流支亦宗唯识,与谛相应。
(11)释彦琮俗姓李,赵郡人,湛深梵文。隋开皇间,总持译事,时梵僧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所译经典,多由琮鉴定。琮著《众经目录》、《西域传》等,义例谨严,对于翻译文体,著论甚详。
(12)玄奘三藏俗姓陈,洛州人。唐太宗贞观二年,冒禁出游印度,十九年归,凡在外十七年。从彼土大师戒贤受学,邃达法相,归而献身从事翻译。十九年间(西纪六四五——六六三)所译经论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如《大般若经》之六百卷,《大毗婆沙》之二百卷,《瑜伽师地论》之一百卷,《顺正理论》之八十卷,《俱舍论》之三十卷。自余名著,具见录中,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比也。事迹具详《慈恩传》中,今不备述。
(13)实叉难陀于阗人。以唐武后证圣间,重译《华严经》,今八十卷本是也,又重译《大乘起信论》等。
菩提流志南印度人。与难陀同译《华严》,又补成《大宝积经》足本。
(14)义净三藏俗姓张,范阳人。以唐咸亨二年出游印度,历三十七年乃归,归后专事翻译,所译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书,至净乃备;密宗教义,自净始传。
(15)不空北天竺人,幼入中国,师事金刚智,专精密藏。以唐开元、天宝间游印度,归而专译密宗书一百二十余卷。
晚唐以后,印土佛教渐就衰落,邦人士西游绝迹,译事无复足齿数。宋代虽有法天、法护、施护、天息灾等数人,稍有译本,皆补苴而已。自汉迄唐,六百余年间,大师辈出,右所述者,仅举其尤异,然斯业进化之迹,历历可见也。要而论之,可分三期:
第一,外国人主译期。
第二,中外人共译期。
第三,本国人主译期。
宋赞宁《高僧传》三集论之云:“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此为第一期之情状。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实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译,全为私人事业,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讹谬浅薄,在所不免。又云:“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此为第二期之情状。鸠摩罗什、觉贤、真谛等实其代表。口宣者已能习汉言,笔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邃典妙文,次第布现;然业有待于合作,义每隔于一尘。又云:“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此为第三期之情状。玄奘,义净等实其代表。我邦硕学,久留彼都,学既邃精,辩复无碍,操觚振铎,无复间然。斯译学进化之极轨矣!
三、翻译所据原本及译场组织
今日所谓翻译者,其必先有一外国语之原本,执而读之,易以华言。吾侪习于此等观念,以为佛典之翻译,自始即应尔尔,其实不然。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盖原本实未著诸竹帛也。《分别功德论》卷第二[1]云:
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
道安《疑经录》云(《出三藏集记》卷五引):
外国僧法,学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
《付法藏因缘传》载一故事,殊可发噱。兹录如下:
阿难游行至一竹林,闻有比丘诵法句偈: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语比丘:“此非佛语。”……汝今当听我演: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语,师告之曰:“阿难老朽,言多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
兹事虽琐末,然正可证印度佛书,旧无写本,故虽以耆德宿学之阿难,不能举反证以矫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无写本之故,不能断言,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传写綦难,故如我国汉代传经,皆凭口说。(二)含有教宗神秘的观念,认书写为渎经,如罗马旧教之禁写新旧约也。佛书何时始有写本,此为学界未决之问题,但据法显《佛国记》云:
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
法显西游,在东晋隆安三年后(西历五世纪初),尚云“无本可写”,则印土写本极为晚出,可以推见,以故我国初期译业,皆无原本。前引《魏略》载“秦景宪从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经”。盖舍口授外无他本也。梁慧皎《高僧传》称安世高“讽持禅经”。称支娄迦谶“讽诵群经”。则二人所译诸经皆由暗诵可知。更有数书,传译程序,记载特详,今举为例:
(一)《阿毗昙毗婆沙》(此书后经玄奘再译为二百卷)。由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见《高僧传》卷一[2])。
(二)《舍利弗阿毗昙》。昙摩耶舍暗诵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书梵文,停至十六年,经师渐娴秦语,令自宣译(见《出三藏集记》卷十[3]引释道标序)。
(三)《十诵律》。罽宾人弗若多罗以秦弘始六年诵出,鸠摩罗什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弃世——西域人昙摩流支以弘始七年达关中,乃续诵出,与什共毕其业(见《高僧传》卷六[4])。
若《毗婆沙》者,经两次口授,两次笔受,而始成立。若《十诵律》者,暗诵之人去世,译业遂中辍,幸有替人,仅得续成。则初期译事之艰窘,可概见矣!
在此种状态之下,必先有暗诵之人,然后有可译之本,所诵者完全不完全,正确不正确,皆无从得旁证反证。学者之以求真为职志者,不能以此而满意,有固然矣!于是西行求法热骤兴。
我国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礼麦加,纯出于迷信的参拜也。其动机出于学问——盖不满于西域间接的佛学,不满于一家口说的佛学。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澥,非自进以探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余尝搜讨群籍,得晋唐间留学印度八十余人(详见《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今摘举数人,考其游学之动机如下:
法护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游历诸国。……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梁僧传》卷一本传)
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西渡流沙。(卷三本传)
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除以宋永初元年……远适西方,进至罽宾国……学梵书梵语。……(卷三本传)
道泰先有沙门道泰,志用强惈,少游葱右,遍历诸国,得毗婆沙梵本十余万偈。……(卷三《浮陀跋摩传》)
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诘,遂周流西国……功逾十载。(卷三本传)
宝云忘身徇道,志欲……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在外域遍学梵书(卷三本传)。
智猛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有方等众经……遂以姚秦弘始六年……出自阳关……历迦唯罗卫及华氏等国,得《大泥洹》、《僧祇律》及余经梵本。(卷三本传)
朱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卷四本传)
玄奘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闻所惑。(《慈恩法师传》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