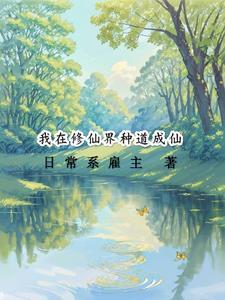19楼乐文小说>阿耶玳,苗语,我们的根 > 第56章 云端梯田(第1页)
第56章 云端梯田(第1页)
I凯寨的晨雾还未散尽,龙安心就被一阵柴油发电机的轰鸣惊醒。他推开木窗,看见三辆印着"中国移动"字样的工程车停在村口老枫树下,十几个穿橙色工装的工人正在卸设备。
"真要建基站了?"龙安心套上沾着泥点的胶鞋,昨晚刚从深圳带回来的行李箱还敞开着,里面民族大学教授给的资料露出一角。
吴晓梅的声音从楼下传来:"阿耶!快来,他们要砍神树!"
龙安心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村口已经围了二十多个村民,务婆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她那件靛蓝色的老苗衣在晨雾中像一面褪色的旗。移动公司的工人们尴尬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图纸和测量仪。
"不是砍树,是在树上装设备。"一个戴安全帽的技术员擦着汗解释,"这是县里定的点,信号能覆盖整个寨子。"
务婆的拐杖重重敲在枫香树裸露的树根上:"这棵树有灵!1958年大炼钢铁时都没人敢动!"
龙安心挤进人群,闻到空气中飘散的柴油味和村民身上的烟叶味混合在一起。他认出那个技术员是县里张副乡长的侄子,去年在乡政府见过。
"阿弟,"龙安心用当地方言打招呼,"能不能换个位置?"
技术员小张如蒙大赦,赶紧展开图纸:"龙哥你看,这里是县里规划的5G覆盖图。这棵枫香树位置最高,不在这里装,整个凯寨都没信号。"
龙安心接过图纸,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和红圈让他想起建筑工地的施工图。吴晓梅凑过来,银耳坠擦过他脸颊,带着五倍子染布特有的酸涩气息。
"他们在说什么?"她指着图纸下方的技术参数。
"说这个基站能让全村上网,视频通话都不卡。"龙安心翻译道,突然想起教授说的直播带货,"还能把我们的绣片卖到更远的地方。"
务婆的耳朵却出奇地灵:"卖绣片?用空气卖?"她嗤之以鼻,"以前没有网,我们的蝴蝶妈妈不也活了几千年?"
人群中有年轻人小声嘀咕:"那是传说。。。"立刻被几个老人瞪得缩了回去。
龙安心突然有了主意。他爬上枫香树旁的石碾子,高度刚好能平视树冠:"大家听我说!"他用苗汉双语交替喊道,"我们不砍树,只在树干上固定设备,像给树戴个银项圈。务婆,您看行不?"
老人眯起眼睛,树皮般的皱纹堆叠在一起。沉默像晨雾一样笼罩着人群,只有发电机在远处突突作响。
"要戴也得戴真的银项圈。"务婆终于开口,"得先祭树。"
小张技术员刚要反对,龙安心一把拉住他:"按苗家规矩来,不然这基站十年也建不成。"
半小时后,务婆带着妇女们在枫香树下摆开祭品:一碗酸汤鱼、三杯米酒、一碟染红的糯米。老猎人阿公从家里取来珍藏的银项圈——据说曾经救过山火中枫香树的命。项圈被郑重其事地挂在树干两米高的位置,正好是待会儿要安装设备的高度。
"开始吧。"务婆用苗语宣布。
妇女们唱起古老的祭树歌,声音低沉如溪水流过卵石。龙安心注意到吴晓梅唱得格外认真,银项圈下的锁骨随着呼吸起伏,像一对欲飞的蝶翅。仪式结束后,小张技术员迫不及待地指挥工人架设设备。
"龙哥,有个问题。"小张挠着头,"我们没带这么高的梯子。。。"
龙安心看了看树干,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掌——三年前工地磨出的老茧还没完全褪去。他吐了口唾沫搓搓手:"我来。"
爬树比想象中困难。枫香树的树皮粗糙得像砂纸,很快就把他的手掌磨得通红。爬到三米高时,龙安心停下来喘口气,无意间俯瞰全村——青瓦木屋像蘑菇一样散落在山间,梯田在晨光中泛着金绿色的波纹,远处务婆家的火塘升起一缕细烟。他突然理解了父亲当年修建鼓楼时的心情:站在高处看家园,会涌起一种奇怪的保护欲。
"再往左一点!"小张的喊声把他拉回现实。
龙安心艰难地调整姿势,配合工人固定设备。汗水流进眼睛,火辣辣的疼。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见下面喊:"好了!"
下树时他的腿已经发抖,掌心磨破了两处,血丝混着树汁,黏糊糊的。吴晓梅默默递来一块蓝靛布手帕,上面绣着星辰纹样。
"快看!"小张突然举着手机欢呼,"有信号了!5G满格!"
人群骚动起来,年轻人纷纷掏出手机。龙安心看见自己的华为手机右上角果然出现了那个小小的"5G"标志。他点开微信,民族大学教授发来的资料包瞬间下载完成——在深圳要加载半分钟的文件,这里只用了一秒。
"龙哥,笑一个!"小张举起相机。
龙安心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吴晓梅拉到枫香树下。她踮起脚尖,迅速拍掉他肩头的树皮屑,又把自己的银项圈摘下来挂在他脖子上。"咔嚓"一声,画面定格:满身树屑的龙安心站在刚装好的基站下,脖子上挂着苗银项圈,背后是参天的古枫香。
谁也没想到,这张照片三天后会出现在县政府的宣传海报上,标题是"数字乡村建设典范:苗族青年勇攀高峰架设信息天路"。
"现在可以直播了吧?"回合作社的路上,吴晓梅兴奋地问。她手里攥着教授送的智能手机,屏幕上还留着下载好的直播软件。
龙安心点点头,掌心火辣辣的痛感让他想起深圳文博会的热闹场景:"试试看。"
下午,他们在合作社门口架起手机。吴晓梅换上节日才穿的绣花衣,银饰擦了又擦。龙安心则穿上那件唯一没补丁的蓝衬衫——袖口还留着深圳酒店的洗衣标签。
"开始咯!"他按下直播键。
屏幕上的数字跳动了几下,最终停在"7"——其中3个是系统默认的机器人观众。唯一一条弹幕飘过:"作秀!现在哪有真苗绣?"
吴晓梅的手抖了一下,碰翻了装酸汤的土碗。深红色的汤汁泼洒在正在绣制的嫁衣上,像一滩刺眼的血。她慌忙去擦,却把绣线也扯乱了。
"别播了。"她低声说,苗语口音比平时更重,"我们像动物园的猴子。"
龙安心默默关闭直播。院子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几只母鸡在啄食晒着的紫米。他想起教授档案里的一句话:"文化传播不是表演,是对话。"
第二天清晨,龙安心背着设备来到务婆家。老人正在火塘边煮茶,茶罐里飘出刺梨和野菊的混合香气。
"阿婆,我想录您唱的古歌。"龙安心架好三脚架,"就是《洪水滔天》那段。"
务婆眯起眼睛:"录了给谁听?"
"给。。。山外的人。"龙安心诚实地说,"他们没见过真的苗歌。"
老人哼了一声,却出人意料地放下茶罐,整理了一下头帕。当龙安心按下录制键时,务婆的歌声突然响起,苍老却有力,像一股从地底涌出的泉水。没有伴奏,没有排练,九十二岁的老人就这样对着镜头唱起了创世史诗。阳光从木窗斜射进来,落在她银白的发髻上,像一顶天然的冠冕。
龙安心用苗汉双语交替翻译歌词,讲到兄妹结婚繁衍人类时,他卡壳了——这该怎么向山外人解释?务婆却突然敲了下火塘边的铜壶:"怕什么?汉人的伏羲女娲不是亲兄妹?"
当天晚上,龙安心把视频剪辑好上传。没有特效,没有字幕,只有务婆布满皱纹的脸和时而激昂时而低吟的歌声。他随手@了几个民族学相关的账号,然后关机睡觉——明天还要去查看刺梨地的长势。
三天后的早晨,龙安心被手机提示音吵醒。吴晓梅在门外激动地敲门:"快看!务婆上电视了!"
准确地说,是上了民族大学的官方微博。那段视频被转发了两千多次,评论区挤满了惊叹:"这才是活史诗!""求完整版!""歌者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是历史!"最让龙安心震惊的是某高校民族学系的留言:"已联系非遗保护中心,请求系统采集这位歌师的古歌。"
合作社突然热闹起来。年轻人围着龙安心问东问西,老人们则忧心忡忡:"那些汉人学者会不会把务婆的'歌魂'偷走?"龙安心用苗汉双语耐心解释数字存档的意义,说到口干舌燥时,吴晓梅端来一碗刺梨汁:"润润喉。"